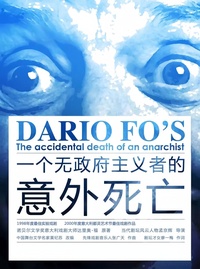孟京輝對達里奧·福戲劇改編研究——以《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為例
這篇劇評可能有關鍵情節透露
達里奧·福在1970年發布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于199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談作品的知人論世觀點來看,達里奧·福自己就是一個左翼作家,他的作品都著鮮明的政治立場、熾熱的批判激情,字里行間充斥著對不合理社會現象的冷嘲熱諷。其劇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既是劇中被嚴刑拷打死去的那個沒出現的人物,也是那個瘋子,更是達里奧·福本人。但是我隱隱感覺,達里奧·福背叛了革命。據說,達里奧·福得到諾貝爾獎以后,大量的讀者和觀眾支持他不去領獎,以表示對權威的反抗,但是達里奧·福還是去了,托詞為他是代表著很多和他一樣的江湖人士去的,他要為他們正名,可見,達里奧·福是一個作家,而且只是一個作家,他寫的東西還真不一定他會去做,他鼓勵別人反對政府,自己卻被“招安”,未免讓讀者心寒。這讓我想到王小波勸他的侄子的故事,他侄子要當藝術家,要去親身上山下鄉體驗“苦難”,他侄子的父母自然是不愿意的,但也勸不動,單單他侄子又很崇拜王小波,說王小波是搞藝術的,會理解他,說服侄子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王小波頭上,王小波略微思考了一下,就說,做藝術不一定要經歷苦難,更多的藝術家只是歌頌別人的苦難就能成功了。這一句話用來形容達里奧·福這個不徹底的藝術家倒是很恰當。
對比原劇本來說,孟京輝改編的還是有點不一樣,原劇本梗概基本是,米蘭火車站發生一起爆炸案,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指控為兇手,審訊期間,他突然跳樓身亡。一名瘋子在警察局偶然接觸到無政府主義者“偶然死亡”的材料,他隨機應變,喬裝成最高法院的代表復審此案,終于洞悉內情。所謂“意外死亡”,竟是警察對無政府主義者嚴刑逼供,將其活活打死后從窗口丟下,造成的畏罪自殺的假象。孟京輝把這個瘋子變成了一個編劇,在劇中是四個警察為了圓謊、樹立人情味形象以及對付民憤,而進行推導一系列的可能去跳樓的原因,最后得出無政府主義者說出“情況太復雜了,現實太殘酷了,理想都破滅了,我也不想活了”的結論,這其中有大量的碎片化有中國文化元素,很多時間節點也容易讓觀眾想到我們也有一個混亂的年代。
一、孟京輝臺詞的造詣
孟京輝的作品更容易讓人笑,最重要的就是他對臺詞的考究,可能與他本人是中文系畢業的有關。比如,他在開頭念白“達里奧·福,放了一個屁,崩到了莫斯科,來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國王正在看戲,聞到了這個屁,很不滿意,找來科學家,研究分析,屁是一股氣,在人的肚子里竄來竄去,一不小心打開后門溜了出去。放屁的人,歡天喜地,聞屁的人,垂頭喪氣,有屁不放,憋壞心臟,沒屁硬擠,鍛煉身體。屁放的響,能當校長,屁放的臭,能當教授,不響不臭,思想落后!”雖然偏激,但卻因為押韻等因素惹人發笑。
他也穿插用了很多方言,北京的有《茶館》王利發、常四爺、秦爺的對話設計,如“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回復:“呦,這不是無爺嗎?”“孫子,打出你丫屎來,你信不信?”回答:“打出來也是你費勁,還得一口一口把他吃了”天津的是“我到了天津衛,嘛也沒學會,學會了開汽車,壓死了二百多,警察來抓我,我說不是我,我連滾帶爬鉆進了女廁所,女廁所沒有燈,我掉到粑粑坑,我跟粑粑做斗爭,差點沒犧牲。”而且在觀看話劇時候,涉及到“屎尿屁”的地方觀眾都會笑。
此外,孟京輝還插入了很多旁白,在導演中心制的談判中,警察局長認為舞臺在警局,而警局里應該聽他的,編劇認為警察局被寫進了劇本里,應該聽達里奧·福的,而這是外面突然傳來“到底應該聽誰的,聽聽良心的吧,聽聽利益的吧,聽聽思想的吧,省得混混噩噩,聽聽本能的吧,以免異想天開,聽聽理想的吧,理想指導現實,聽聽規律的吧,昨天決定明天, 聽聽平等的吧,誰都不低人一等,聽聽差別的吧,誰都不高人一等,聽聽正義的,正義糾正世界。”這段旁白看的時候雖然不明就里,但又沒什么違和感,可能這也是孟京輝在先鋒主義道路上關于戲劇形式的探索。
在故事最后,為了解釋幫兇產生原因,編劇喊出:“事情當然不能怪你們,事情雖然是你們干的,但教唆的是他們怪他們。誰們?說的遠一點,山頂洞人,說的近一點,你們家人。說的唯物一點,日蝕月蝕。說的違心一點,儒家法家,說的辯證點,受害人,說的痛快一點,都是別人。”結尾處文字游戲,讓人體會到孟京輝反抗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體制,似乎是在和一個扎根在人們心中的文化基因做斗爭。
二、孟京輝與觀眾的對話
傳統戲劇理論中的“第四堵墻”將舞臺與觀眾席分割,把兩者無形地隔開,從而營造演出的幻覺氣場并保證觀眾的旁觀地位。隨著戲劇作為劇場藝術的本質漸漸被戲劇家深度認識,戲劇的表演空間不斷地被挖掘、被擴展,從打破“第四堵墻”的探索,到根本不承認“第四堵墻”存在的實驗,觀眾理應成為劇場組成部分的觀念愈來愈被戲劇工作者重視。而布萊希特便是要推翻“第四堵墻”,推翻舞臺要營造的幻覺氣場,強調“陌生化”,要求演員與角色分離。如何調動久存旁觀意識的觀眾參與到戲劇氛圍中,同時又要避免被“拒絕”的尷尬,孟京輝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在要求樹立警察形象要求提出的同時,扮演編劇的演員直接跑到到觀眾席的黑暗里,讓舞臺上的警察尋找,并且藏在觀眾中與警察對罵。“無政府主義者,你丫出來呀,我看見你了”這樣,觀眾無意間就成為戲劇所歌頌的人民的一員。觀眾與編劇站在同一陣營,同編劇一起戰斗,他們門似乎成為編劇的強大后盾。觀眾被納入表演空間,提升了榮辱感,更容易與劇中人物產生情感共鳴。最后得出,“我被感召了,我上來了。”
在最后的結尾處,警察局長對著對著觀眾吶喊,“那些吆五喝六算人物的,那些不明不白成為富翁的,那些油頭粉面為太子的,那些珠光寶氣當小妾的,咱們深一腳淺一腳的巡邏,青一塊紫一塊的出擊,還不是為了他們有一搭沒一塔的胡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戲,要不是我們發現一處漏洞,堵住一處漏洞,發現一只螞蟻,碾死一只螞蟻,他們有戲看嘛?他們有戲唱嘛?”訴苦警察局立功不易,這一段不僅是警察局作為“走狗”的吐槽,更多的是面對觀眾在演戲,暗指觀眾在現實中其實就是幫兇,這里的他們,肯定是包含觀眾自己的階層的,這段戲中戲,在現場得到觀眾的喝彩聲,看來戲劇觀眾也喜歡自己批判自己。
在戲劇有一段四人坐著火車跑的時候唱起的兒歌,歌詞大概如下,“美國的月亮圓又圓,美國的鈔票滿天飄,山姆大叔彈起琴,自由女神把舞跳。”讓人不僅拍座叫好,一是因為在意大利坐火車根本去不了美國(歐洲和美洲隔著大西洋呢),諷刺了當時國內一些人根本不知道美國在那,就說美國好的的言論,而是看戲劇的比較都是相對“中產”的人,面對著觀眾,不免含有揶揄的意味在里面,不管怎么樣,觀眾里向往美國的可不少;這把諷刺美國夢的意識形態做的一流。
三、孟京輝批判的力度
孟京輝和原著的改編很大的不同就是,孟京輝自己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批判,比如他在劇中設計的臺詞有諷刺先鋒主義的,但他自己也是先鋒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實我頂看不上那些先鋒派,在舞臺上搞十個八個破電視,把舞臺上搞的廢品站不廢品站,收購站不是收購站,如今還有在舞臺上砌水池子的,還有人把屋頂都搬上了舞臺,分明是現實主義的功力不夠,所以才來嘩眾取寵。”我自己在舞臺上罵我自己,一方面是回應自己面對的質疑,另一方面,自己確實在國內的先鋒主義有一定的話語權,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嘲并不能解決困境,只能消解困境。如果是先看戲劇,再看劇本,很不容易理解孟京輝的穿插的很多東西。
在劇場開始的時候,介紹了達里奧·福的生平、戲劇界對于達里奧·福的褒貶不一,以及在劇場設計中有一個達里奧·福的漫畫肖像,以及在戲劇的間隔,孟京輝(其中有一個是他自己)都會安排兩個念旁白的人員配上解說詞、詩歌、影像的方式斷開故事情節,讓觀眾隨時從劇情中抽離出來,都是在一遍遍告訴觀眾,這是在致敬經典,不是在說本國的事情,批判政治色彩少了那么幾分。
雖然在政治上批判孟京輝力度較弱,但是對于現實經濟的貧富差距,孟京輝顯然沒有要避開的意思。這就有點像傳播學法蘭克福學派到文化研究學派的轉變一樣,既然不能推翻你,那就選擇批判那你創造的這個社會。比如,劇中出現警察甲由于害怕自己打死人的時候,警察局長說到“看看你那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否提首長心里多喜歡了,我真想代表全世界的富人,認你當干兒子給壓歲錢。”還有就是對于有錢父親的恭維,為了父親的金錢、地位,不能讓父親死,批判“孝順是假,追逐權勢是真”的社會現象;以及說到“長大了要想騎人的脖子,必須要有一個像樣的爸爸才可以”,這個“騎人”,一語雙關,既是富人對窮人的壓迫,也內涵兒子對父親的要挾。作文題目《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忙的人,我在電視機看到他比在家里看到的時候多。”讓人想到開心麻花前幾年的電影《夏洛特煩惱》中男配角袁華的橋段,袁華得了行政區作文第一名,題目是《我的區長父親》,讓人發笑的同時又讓人驚醒,不僅讓我想到臧克家在紀念魯迅先生時寫道“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給人民作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四、孟京輝的對人民的態度
原著的瘋子提到“這么說來,你們還向電視臺和報界撒了謊,說兇手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是捏造的,你們掌握了很有分量的線索,是嗎?你們使用計謀,設下圈套,搞陰謀詭計,不僅僅是為了制服犯罪嫌疑人,而且是為了欺騙、愚弄善良的,傻瓜似的老百姓!”“總而言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沒有丑聞的時候,就需要制造出丑聞來,因為這是讓被壓迫者宣泄自己的情緒,維護政權的最奇妙的手段。而孟京輝的劇中也改編到“這不是明擺著的嗎,一個沒權沒勢的在押犯人,不先鋒他怎么成為這兒的嘉賓,這個嘉賓,不徹頭徹尾的荒誕,他憑什么要跳樓,你們搞陰謀詭計,設下圈套,不僅僅是為了陷害當事人,更是為了愚弄、欺騙傻瓜式的老百姓的信任。”表明了自己站在人民立場的創作,他的選擇是代表人民的聲音 ,替人民說話。
在將近結尾中的吟誦中,孟京輝敘述了達里奧·福妻子被人侮辱的故事,轉而反問“在米蘭的大街上要不要帶刀,在有著棕櫚樹的米蘭的大街上要不要帶刀,在陽光燦爛天空湛藍的米蘭要不要帶刀,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大街上要不要帶刀?在21世紀的米蘭大街上要不要帶刀?在這世界上善良的人們,卑賤的人們、恭順的人們、軟弱的人們,在米蘭的大街上,別忘記帶防身的刀,在這世界上善良的人們、卑賤的人們、恭順的人們、軟弱的人們,永遠不要忘記強權和壓迫還不曾被消滅,在這世界上善良的人們、卑賤的人們、恭順的人們、軟弱的人們,拿起你們的刀劍砍向世界的不公。”孟京輝顯然是不滿意人們沉醉娛樂化的世界,他鼓勵人們進行反抗,即使無力,但是卻悲壯的。
孟京輝雖然希望人民覺醒,但似乎他還是在作品中暗含了一絲失望,這一點可以在原作中象征正義的女記者被編成一個舞女浪的情節中看到,顯然是與達里奧·福本意不相符合的。如原劇本中說到“誰也不會理睬這些...最重要的是要引發丑聞...不管您是否樂意!意大利人將和美國人、英國人一樣,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成為現代人,并且最終能夠大聲呼吁道:“是的,我們被糞便淹沒到了脖子,正因為如此,我們將昂首挺胸前進!”以及達里奧·福回應為什么這部劇會這么火爆的時候,回答道,至少,是源自權力機關顛倒是非、捏造事實的偽善謊言,特別是源自他們對國家制度的恣意踐踏。我們清醒地知道,我們的鋌而走險可能被告發、被指控、被起訴。但無論如何,我們的行動是值得的。正如貝爾托·布萊希特所說:“黑暗時代中,我們揭露黑暗,美好時代才會到來。可見達里奧·福并不是純粹的批判,而是建設性的意見,孟京輝的悲觀主義在劇本改編中可見一斑。
五、結語
綜上來說,孟京輝改編的版本在臺詞、與觀眾互動(打破第四堵墻)有著一定的先鋒作用,但是在情節邏輯上,中間存在很大一部分“跑調”,更不必說在政治批判力度以及人民性上的不足,或許孟京輝自己的話可以為本文收尾:“分明是現實主義的功力不夠,所以才來嘩眾取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