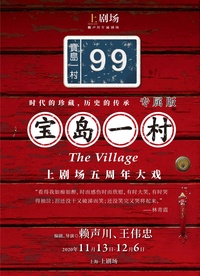民族的傷疤
一場內戰,造就了無數個家庭的悲劇,母親的兒子去了臺灣,妻子的丈夫去了臺灣。離開的時候他們都說,只是去幾天啦,很快就打回來了,但是他們都撒了謊,這一去,是40年。
王偉忠生于眷村,長于眷村,他很想把這些故事表達出來,對于他人而言,是一個青春的故事。對于他,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1949年國軍敗走大陸,幾百萬公教軍人員以及家屬隨同來臺。底層士兵在慌亂中重組家庭,住進眷村,開始新的生活。
物質的匱乏,精神的失落,都不能阻止他們在絕望中收拾起生活,一點一滴的開始。來自各個省份,言語難通,卻有類似的經歷。鄰里之間,有互相扶持,有互相埋怨,到最后剩下的還是一輩子的感情。
一度被蔣委員長承諾的反攻大陸,勿忘在莒的目標激勵著,幻想著回到自己的家鄉,直到蔣公逝世,一切諾言都已經破滅。老兵們都在哭,哭蔣委員長的離世,更是哭自己夢想的破滅,哭著此生難返故鄉。
當然,生活還是要繼續。
80年代,大陸開放探親,多少人的父母已經不在人世,多少人的妻兒已經開枝散葉。多少桑海滄田。國共決裂40年,說來也不是多長的時間,對很多人而言,竟是一生。甚至,直至離世都沒有回到故土,都沒有再見父母兄妹一面。
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始,以眷村為背景的故事接連上演。但是對于大陸觀眾而言,最感觸的除了共有的人性感觸以外,最動人的還是那場內戰,兄弟鬩墻,從來都不光彩,更可怕的是這場內戰讓數以百萬人骨肉分離,經世不得相見。
當主角40年后回到上海,父母已經逝世,他跪在墳頭,失聲哭泣,從未想過,那次分離,竟是最后一次凝視父母的面容。此時,我聽到身邊昏暗的座位里四起的啜泣聲。
王偉忠生于眷村,長于眷村,他很想把這些故事表達出來,對于他人而言,是一個青春的故事。對于他,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1949年國軍敗走大陸,幾百萬公教軍人員以及家屬隨同來臺。底層士兵在慌亂中重組家庭,住進眷村,開始新的生活。
物質的匱乏,精神的失落,都不能阻止他們在絕望中收拾起生活,一點一滴的開始。來自各個省份,言語難通,卻有類似的經歷。鄰里之間,有互相扶持,有互相埋怨,到最后剩下的還是一輩子的感情。
一度被蔣委員長承諾的反攻大陸,勿忘在莒的目標激勵著,幻想著回到自己的家鄉,直到蔣公逝世,一切諾言都已經破滅。老兵們都在哭,哭蔣委員長的離世,更是哭自己夢想的破滅,哭著此生難返故鄉。
當然,生活還是要繼續。
80年代,大陸開放探親,多少人的父母已經不在人世,多少人的妻兒已經開枝散葉。多少桑海滄田。國共決裂40年,說來也不是多長的時間,對很多人而言,竟是一生。甚至,直至離世都沒有回到故土,都沒有再見父母兄妹一面。
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始,以眷村為背景的故事接連上演。但是對于大陸觀眾而言,最感觸的除了共有的人性感觸以外,最動人的還是那場內戰,兄弟鬩墻,從來都不光彩,更可怕的是這場內戰讓數以百萬人骨肉分離,經世不得相見。
當主角40年后回到上海,父母已經逝世,他跪在墳頭,失聲哭泣,從未想過,那次分離,竟是最后一次凝視父母的面容。此時,我聽到身邊昏暗的座位里四起的啜泣聲。
有關鍵情節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