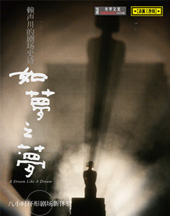哪里似夢?
之前只看過一部《暗戀桃花源》,雖然由于看得時間太晚(2011年左右)已經失去了應有的驚喜,加上當時“桃花源”的部分是戲曲的改編,些許覺得有些用力過度。但是考慮到創作的年代,對賴聲川的出品還是信任的。自然春節前《如夢之夢》的宣傳轟炸讓我覺得這是今年不得不看的一部話劇,早早的買了票等著被驚艷。意外的是:在前期的宣傳上劇情內容反倒被放到了其次。一邊嚷嚷著“史詩巨制”一邊對“史詩”的內容只字不提。就感覺像是一個以號稱以長跑見長的運動員最后穿著高級定制的運動服不痛不癢的參加了跳高項目一樣怪異。四月十日十一日連續兩晚的觀劇經歷卻讓人非常不舒服;網上種種過譽的褒贊,更是加重了這種不舒服。
影評人周黎明稱之為“賴聲川的一次革命性實驗”,在不去考證是否“革命性”的前提下,還是中肯的。該劇宣傳吸睛的三個亮點:時長,環形舞臺和眾多明星,僅前兩項在形式上就是極大的突破。為了滿足時間和空間上的大跨度,利用環形舞臺和前后左右(又各搭建一個二層樓的基本形,可樓上樓下單獨使用增加舞臺層次),洋洋灑灑的鋪開了三十多個子場景,從醫院、電影院、法國酒館、城堡、碼頭、小閣樓、妓院等等到甚至飛機起飛,火車相撞等場景也是惟妙惟肖的,布景、燈光和音響算是配套用重金砸出了升華。
對于超時長和環形舞臺的實驗結果:媒體人于困困曾調侃到:“但凡渾然天成的藝術家,都需要一個制作人/編輯/或其懂行的人,能痛下黑手把藝術家那些濫情的枝節全部修剪掉。”《如夢之夢》就像是一個天生骨骼精奇卻長了滿身肥肉的小子,要成為一代宗師,不光要減掉身上多余的肥膘,還得好好練練肌肉才行。超時長的原因歸結于對劇本過多無用細節舍棄的吝嗇,整個觀劇的體驗變成要享受20分鐘的快感必須以犧牲60分鐘的拖沓冗長為代價的拉鋸戰。環形劇場本是我觀劇前最大的期待,可是購票的時候發現蓮花池座票矯情的賣到了2013元/場,該劇還需要上下兩場單獨買票。這樣一來,想看完整場得花掉4026塊大洋。像大部分迫于現實壓力的愛好者一樣,能承受范圍內的票全部集中在了2樓甚至3樓的中后排。有人會說,賣票的部分跟劇本身無關。可是當因為票價的天塹,一直看不到演員的臉,甚至要靠超低像素的幻燈投影來完整觀劇的時候,你還會說跟劇無關么?而且據蓮花池座的網友透露,連續兩晚長達四個小時坐在完全不舒服的轉椅上不停的轉動還要一直抬著頭仰視表演的經歷也是一種苦行僧般的修煉。試問,會有哪部舞臺劇是以犧牲觀眾的觀劇體驗為代價的?在演出單上,有一段賴聲川于2000年1月創作前期的話:“(這些年來)為大眾的觀眾創作… …我的實驗精神總是被限制在某些基本的經濟界限之內。這次作品,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讓想象力自由奔跑,不受此邊界的拘束。到目前為止,感覺自己非常被解放。”斥巨資打造的環形舞臺,雖然達到了不同凡響的舞臺效果,但是演員表演的信息量和觀眾觀劇接受的信息量之間卻大打折扣,付出與回報的性價比并沒與質的飛躍,這樣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的安排究竟是否有意義,還請賴導和制作單位掂量。
另一個形式大于內容的部分即是選角。平心而論,李宇春、胡歌和許晴等明星在表演上可謂是盡職,亦可說還頗有亮點。但誠懇的說,以李宇春的角色曉梅舉例,李并不是那個“有且僅有”的曉梅。都說成功的演出是演員和角色是長在一起的,譬如成蝶衣之于張國榮,小燕子之于趙薇。回顧曉梅的臺詞和動作,可以是任何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內向年輕女子,甚至我覺得是個扎辮子的樸素女孩更為貼切合適,強硬相親的情節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出戲。
除了過于豐腴的形式感,真正讓我覺得本劇名不符其實的,是導演對劇情推進和角色刻畫的粗暴草率。表演流于表面,常常會間歇性的突然激動不已,用極快的語速表達自己內心的澎湃和激動(譬如“第七顆煎蛋的軌道”部分的江紅,一直不停的重復“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但是每每看到不管是病人家屬、建筑師、淑女、妓女、伯爵夫人、伯爵、小女仆還是其他什么角色都用同樣的表演技巧表達的時候,很難不覺得這些形象都想熨斗熨燙過一樣平。除了表演方式,臺詞的描寫更是有助于這種沒有生活痕跡和性格褶皺的平坦,我依稀記得伯爵和伯爵夫人分手晚餐的對話:
我不愛你了,我們分開吧
告訴我,她是誰!?
你快樂么?你根本不快樂!
我可以忍… …
… …(我忘了…)
告訴我,她是誰!?
她是誰!?
這樣的對話完全沒有任何角色特點,你說他們是伯爵和夫人,我怎么覺得可以是當代都市里的任何一對男女?臺詞沒有性格,直接導致人物沒有性格,需要隱忍、克制的特點沒有體現出來,如何去演繹后面老謀深算的伯爵和暗渡陳倉絕地反擊的顧香蘭?按照《如夢之夢》的“骨架”,除了那一幫瘋瘋癲癲的藝術家外,幾個主要的角色應該是內斂深沉的形象才會更有張力。早早的就在大腦門兒上貼上了“薄情”、“記仇”的標簽,已經提起來的提防直接斬殺了后面該有的驚喜。
寫這篇文章之前,在網上看到了一篇題為《導演賴聲川談<如夢之夢>:知死亡才知珍惜人生》這樣的采訪:
“(賴聲川)說到生死,好像寫下來就很沉重,沒人想看了。我覺得大家可以接近這個題目。比如李宇春的第一個獨白,學了7年醫科,但沒人教她面對人生中這件唯一會發生的事:死亡。很多戲劇是在逃避生命,而《如夢之夢》是在直面生命和死亡。我不會逼迫你去思考,但我會用一個很能接受的方式讓你自愿走入情境。”
我不知道賴導從哪里聽來的學了七年醫科沒有人教如何直面死亡,但是凡是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不是真的。為了達到塑造一個被死亡嚇壞了的新手醫生的角色,賴導竟然可以連常識都不要了,硬生生的扔給李宇春這么一個莫名其妙的心理包袱。更可笑的是,為了緩解這樣的心理負擔,曉梅去求助于旅行藏區的叛逆表妹,這個還帶著一副天真浪漫嗓音,不諳世事的姑娘教授的“自他交換”的理由竟然是“反正,試試嘛~”還是一副舔著棒棒糖坐在秋千上蕩漾的形象。除此之外,還有為了塑造江紅孑然一身的孤寂感非要套上一個“黑奴偷渡,僥幸生還”的故事;為了體現顧香蘭在法國時期的“自由奔放”非讓她甩著無力的胳膊做抽象派,還讓一個更像是烤羊肉串的小胡子佯做達利在旁邊呼喊“香蘭,你自由了~”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由于這種欠考慮的堆砌,對劇本稍有要求,就會發現人物性格讓人難以信服,兼帶著那些莫名其妙的愛情又莫名其妙的不愛,莫名其妙的自由反叛更不用說那些像沒剪干凈的線頭一樣莫名其妙的線索,其中一半斷得尷尬(譬如莫名其妙出走的同性戀前妻,突然出生又突然死去的兒子,聽故事的小護士,突然死去又突然出現的王德寶),另一半則抓不到撓撓不著的類似和模糊不清的宿命感(譬如前妻和顧香蘭,江紅跟顧香蘭,伯爵跟五號病人)。
按照周黎明老師的說法,該劇創作的時間早于《云圖》,甚至早于《云圖》的原著(2004),只不過有一個表現上佳的《云圖》在前,整個《如夢之夢》的表現顯得雞肋:你說它不創新肯定是冤枉死了,可是究竟有什么難得的新意,又難以言表。整劇上本基本上是個嵌套式的結構,下本則偏重于顧香蘭的傳奇人生。從分場上來看,這樣取巧的結構,至少只看了其中一場都不會覺得突兀或者莫名其妙的太厲害;同一人物的不同時期同臺的呈現方式不光拉出了時間上的層次,也是為了讓新來的觀眾快速入戲隨時補充背景信息。只不過,我一直固執的認為,只有表演不出來的內容才靠這個最笨的辦法借一張旁白的嘴巴。
“在一個故事里,有人做了一個夢;在那個夢里,有人說了一個故事。”這是演出單上劇情簡介部分的第一句話,不怕再多說一句不贊同的觀點:全劇都是故事,哪里有夢?
影評人周黎明稱之為“賴聲川的一次革命性實驗”,在不去考證是否“革命性”的前提下,還是中肯的。該劇宣傳吸睛的三個亮點:時長,環形舞臺和眾多明星,僅前兩項在形式上就是極大的突破。為了滿足時間和空間上的大跨度,利用環形舞臺和前后左右(又各搭建一個二層樓的基本形,可樓上樓下單獨使用增加舞臺層次),洋洋灑灑的鋪開了三十多個子場景,從醫院、電影院、法國酒館、城堡、碼頭、小閣樓、妓院等等到甚至飛機起飛,火車相撞等場景也是惟妙惟肖的,布景、燈光和音響算是配套用重金砸出了升華。
對于超時長和環形舞臺的實驗結果:媒體人于困困曾調侃到:“但凡渾然天成的藝術家,都需要一個制作人/編輯/或其懂行的人,能痛下黑手把藝術家那些濫情的枝節全部修剪掉。”《如夢之夢》就像是一個天生骨骼精奇卻長了滿身肥肉的小子,要成為一代宗師,不光要減掉身上多余的肥膘,還得好好練練肌肉才行。超時長的原因歸結于對劇本過多無用細節舍棄的吝嗇,整個觀劇的體驗變成要享受20分鐘的快感必須以犧牲60分鐘的拖沓冗長為代價的拉鋸戰。環形劇場本是我觀劇前最大的期待,可是購票的時候發現蓮花池座票矯情的賣到了2013元/場,該劇還需要上下兩場單獨買票。這樣一來,想看完整場得花掉4026塊大洋。像大部分迫于現實壓力的愛好者一樣,能承受范圍內的票全部集中在了2樓甚至3樓的中后排。有人會說,賣票的部分跟劇本身無關。可是當因為票價的天塹,一直看不到演員的臉,甚至要靠超低像素的幻燈投影來完整觀劇的時候,你還會說跟劇無關么?而且據蓮花池座的網友透露,連續兩晚長達四個小時坐在完全不舒服的轉椅上不停的轉動還要一直抬著頭仰視表演的經歷也是一種苦行僧般的修煉。試問,會有哪部舞臺劇是以犧牲觀眾的觀劇體驗為代價的?在演出單上,有一段賴聲川于2000年1月創作前期的話:“(這些年來)為大眾的觀眾創作… …我的實驗精神總是被限制在某些基本的經濟界限之內。這次作品,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讓想象力自由奔跑,不受此邊界的拘束。到目前為止,感覺自己非常被解放。”斥巨資打造的環形舞臺,雖然達到了不同凡響的舞臺效果,但是演員表演的信息量和觀眾觀劇接受的信息量之間卻大打折扣,付出與回報的性價比并沒與質的飛躍,這樣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的安排究竟是否有意義,還請賴導和制作單位掂量。
另一個形式大于內容的部分即是選角。平心而論,李宇春、胡歌和許晴等明星在表演上可謂是盡職,亦可說還頗有亮點。但誠懇的說,以李宇春的角色曉梅舉例,李并不是那個“有且僅有”的曉梅。都說成功的演出是演員和角色是長在一起的,譬如成蝶衣之于張國榮,小燕子之于趙薇。回顧曉梅的臺詞和動作,可以是任何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內向年輕女子,甚至我覺得是個扎辮子的樸素女孩更為貼切合適,強硬相親的情節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出戲。
除了過于豐腴的形式感,真正讓我覺得本劇名不符其實的,是導演對劇情推進和角色刻畫的粗暴草率。表演流于表面,常常會間歇性的突然激動不已,用極快的語速表達自己內心的澎湃和激動(譬如“第七顆煎蛋的軌道”部分的江紅,一直不停的重復“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但是每每看到不管是病人家屬、建筑師、淑女、妓女、伯爵夫人、伯爵、小女仆還是其他什么角色都用同樣的表演技巧表達的時候,很難不覺得這些形象都想熨斗熨燙過一樣平。除了表演方式,臺詞的描寫更是有助于這種沒有生活痕跡和性格褶皺的平坦,我依稀記得伯爵和伯爵夫人分手晚餐的對話:
我不愛你了,我們分開吧
告訴我,她是誰!?
你快樂么?你根本不快樂!
我可以忍… …
… …(我忘了…)
告訴我,她是誰!?
她是誰!?
這樣的對話完全沒有任何角色特點,你說他們是伯爵和夫人,我怎么覺得可以是當代都市里的任何一對男女?臺詞沒有性格,直接導致人物沒有性格,需要隱忍、克制的特點沒有體現出來,如何去演繹后面老謀深算的伯爵和暗渡陳倉絕地反擊的顧香蘭?按照《如夢之夢》的“骨架”,除了那一幫瘋瘋癲癲的藝術家外,幾個主要的角色應該是內斂深沉的形象才會更有張力。早早的就在大腦門兒上貼上了“薄情”、“記仇”的標簽,已經提起來的提防直接斬殺了后面該有的驚喜。
寫這篇文章之前,在網上看到了一篇題為《導演賴聲川談<如夢之夢>:知死亡才知珍惜人生》這樣的采訪:
“(賴聲川)說到生死,好像寫下來就很沉重,沒人想看了。我覺得大家可以接近這個題目。比如李宇春的第一個獨白,學了7年醫科,但沒人教她面對人生中這件唯一會發生的事:死亡。很多戲劇是在逃避生命,而《如夢之夢》是在直面生命和死亡。我不會逼迫你去思考,但我會用一個很能接受的方式讓你自愿走入情境。”
我不知道賴導從哪里聽來的學了七年醫科沒有人教如何直面死亡,但是凡是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不是真的。為了達到塑造一個被死亡嚇壞了的新手醫生的角色,賴導竟然可以連常識都不要了,硬生生的扔給李宇春這么一個莫名其妙的心理包袱。更可笑的是,為了緩解這樣的心理負擔,曉梅去求助于旅行藏區的叛逆表妹,這個還帶著一副天真浪漫嗓音,不諳世事的姑娘教授的“自他交換”的理由竟然是“反正,試試嘛~”還是一副舔著棒棒糖坐在秋千上蕩漾的形象。除此之外,還有為了塑造江紅孑然一身的孤寂感非要套上一個“黑奴偷渡,僥幸生還”的故事;為了體現顧香蘭在法國時期的“自由奔放”非讓她甩著無力的胳膊做抽象派,還讓一個更像是烤羊肉串的小胡子佯做達利在旁邊呼喊“香蘭,你自由了~”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由于這種欠考慮的堆砌,對劇本稍有要求,就會發現人物性格讓人難以信服,兼帶著那些莫名其妙的愛情又莫名其妙的不愛,莫名其妙的自由反叛更不用說那些像沒剪干凈的線頭一樣莫名其妙的線索,其中一半斷得尷尬(譬如莫名其妙出走的同性戀前妻,突然出生又突然死去的兒子,聽故事的小護士,突然死去又突然出現的王德寶),另一半則抓不到撓撓不著的類似和模糊不清的宿命感(譬如前妻和顧香蘭,江紅跟顧香蘭,伯爵跟五號病人)。
按照周黎明老師的說法,該劇創作的時間早于《云圖》,甚至早于《云圖》的原著(2004),只不過有一個表現上佳的《云圖》在前,整個《如夢之夢》的表現顯得雞肋:你說它不創新肯定是冤枉死了,可是究竟有什么難得的新意,又難以言表。整劇上本基本上是個嵌套式的結構,下本則偏重于顧香蘭的傳奇人生。從分場上來看,這樣取巧的結構,至少只看了其中一場都不會覺得突兀或者莫名其妙的太厲害;同一人物的不同時期同臺的呈現方式不光拉出了時間上的層次,也是為了讓新來的觀眾快速入戲隨時補充背景信息。只不過,我一直固執的認為,只有表演不出來的內容才靠這個最笨的辦法借一張旁白的嘴巴。
“在一個故事里,有人做了一個夢;在那個夢里,有人說了一個故事。”這是演出單上劇情簡介部分的第一句話,不怕再多說一句不贊同的觀點:全劇都是故事,哪里有夢?
有關鍵情節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