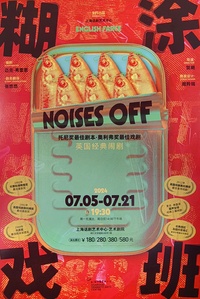必須把第三幕演“活”
昨天去參加了中心關于本劇的Q&A,通過導演和演員們的進一步闡釋,很多之前的看法得到了明確。的確,作為一部經典喜劇,這部劇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正如某些觀眾說的,他們來看一遍就可以發現有新的收獲,可以說這部劇還是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因為這是一部“活”劇,之前看完之后第一感覺就是第一幕和第二幕很充實,由于第三幕有部分是第一幕的重復,所以到第三幕觀眾就會感到劇情略顯單薄,更多的是趨向于無厘頭,也正如導演說的,到了第三幕,編劇本身也沒有什么大招,而事實恰恰相反,這三幕劇活就活在第三幕,從客觀因素上講,這部劇是邁克·弗雷恩早期的成名作品,而相對于后來十分成熟的《哥本哈根》,確實有其缺陷性,但其實這兩部劇的構架是一樣的,在《哥本哈根》中作者將海森堡和玻爾的會面重復了三遍,從不同的層面角度,但是是層層遞進的,這種立體的深化并沒有在《糊涂戲班》中呈現,這也是第三幕的局限性所在,看似是一場對于之前的變本加厲,戲劇性卻在及其缺乏邏輯性的荒誕中被弱化。之前兩幕的精彩在于其幕前幕后連貫性,戲里戲外的呼應,但其實有前兩幕的基礎,第三幕卻是很活的,源于幕后的不可知性,它的活在于之前荒謬性給了這幕更大的發揮空間,但必須承載之前的邏輯性,所以要找回這種邏輯性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之前的那些呼應中找尋新的呼應,第一幕和第三幕的呼應,那些道具,甚至是可以是一種新的原創,但并非簡單到把之前的什么變成一個花瓶,甚至可以在第一幕中添加新的道具以尋求呼應點,而且是相反的效果。這些很好找,把沙丁魚的出現和消失捋一遍就可以找到很多。甚至像墻上那副畫,它甚至可以在第一幕時就掉下來,而在第三幕時由于后臺的混亂沒有掉下來,那種混亂不僅僅是演員的,甚至可以帶動道具、燈光、音效一起的。說到音效我感覺之前看第三幕時小偷三次破窗而入那個音效是個非常大的Bug,照邏輯不可能每次玻璃聲的音效都配上,因為音效師此時肯定也被場上的混亂所影響,很有可能第二次是沒有聲音,或者聲音是延遲的,那也會將是一個笑點,而第三次當導演親自上場時,他一伸手捅破玻璃也是沒有聲音的,他會對音效師報以憎恨的一眼,然后音效師反應過來配上聲音,但導演又被在場的另兩個小偷驚訝了,而邊上可能又有一個演員急于救場混亂中摔了一只酒杯(為制造玻璃聲),而導演和所有人再次受到心理打擊,但一個停頓后又繼續開始演。
除此之外,深度依舊是一個難點,因為喜劇中夸張的表演本身就是為了掩蓋角色內心的淺薄而創造出來的,所以到第三幕,那種夸張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限度,而荒誕派則正是通過這種極度的夸張用強化極簡的方式呈現角色的悲涼,那種令人發笑卻源自于人物內心的真實的薄弱。昨天在現場導演也坦言對于一部喜劇來說這種深度很難,但我覺得還是可以把握的,其實喜劇和荒誕劇之間并沒有非常明顯的界限,不過在現場導演提了一個相當好的想法,就是他說他很想將演員的努力救場表達出來,來體現他們的職業精神,一種幕后我是個凡人,但在臺前,我還有我作為一個演員的精神,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演繹。這將是一個相當好的突破口。因為在第三幕中大多數演員都或多或少因為幕后的原因而受傷了(戲中),他們可以在幕后受傷但在臺前為掩飾而故意“表演”受傷的原因,比如如果那副畫在非常規時間掉下來或是演員可以故意把畫弄掉下來表示自己受傷了,配以“啊,我受傷了”之類,或是在場上通過他人的配合故意制造傷殘的原因,我記得之前有看過TNT的一部莎劇巡演,具體劇目記不清了,由于是改編劇,劇中也是穿插了一個三流劇團的編排和表演,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一段一個演員幾近“自殘”的表演,他要表達一種悲壯的死,但場下的觀眾卻笑得都快崩壞了,演員表演的無虐不施,無所不做的“犧牲”恰恰迎來了觀眾最熱烈的掌聲。這是非常得以借鑒的,以此來體現演員在舞臺上的“犧牲”以及“我們也是人”的表達。
另外,對于那個小胖墩的表演,舞臺劇“一仆二主”中主人公的表演十分可以借鑒,而且極具觀賞性,尤其在表現他要聽命于不同人物的命令時的那種精分。
畢竟這是人家二十年前的戲了,創新是必須的,非常同意導演和劇組的編排思路,同時也非常期待這部劇明年的重排。
除此之外,深度依舊是一個難點,因為喜劇中夸張的表演本身就是為了掩蓋角色內心的淺薄而創造出來的,所以到第三幕,那種夸張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限度,而荒誕派則正是通過這種極度的夸張用強化極簡的方式呈現角色的悲涼,那種令人發笑卻源自于人物內心的真實的薄弱。昨天在現場導演也坦言對于一部喜劇來說這種深度很難,但我覺得還是可以把握的,其實喜劇和荒誕劇之間并沒有非常明顯的界限,不過在現場導演提了一個相當好的想法,就是他說他很想將演員的努力救場表達出來,來體現他們的職業精神,一種幕后我是個凡人,但在臺前,我還有我作為一個演員的精神,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演繹。這將是一個相當好的突破口。因為在第三幕中大多數演員都或多或少因為幕后的原因而受傷了(戲中),他們可以在幕后受傷但在臺前為掩飾而故意“表演”受傷的原因,比如如果那副畫在非常規時間掉下來或是演員可以故意把畫弄掉下來表示自己受傷了,配以“啊,我受傷了”之類,或是在場上通過他人的配合故意制造傷殘的原因,我記得之前有看過TNT的一部莎劇巡演,具體劇目記不清了,由于是改編劇,劇中也是穿插了一個三流劇團的編排和表演,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一段一個演員幾近“自殘”的表演,他要表達一種悲壯的死,但場下的觀眾卻笑得都快崩壞了,演員表演的無虐不施,無所不做的“犧牲”恰恰迎來了觀眾最熱烈的掌聲。這是非常得以借鑒的,以此來體現演員在舞臺上的“犧牲”以及“我們也是人”的表達。
另外,對于那個小胖墩的表演,舞臺劇“一仆二主”中主人公的表演十分可以借鑒,而且極具觀賞性,尤其在表現他要聽命于不同人物的命令時的那種精分。
畢竟這是人家二十年前的戲了,創新是必須的,非常同意導演和劇組的編排思路,同時也非常期待這部劇明年的重排。
有關鍵情節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