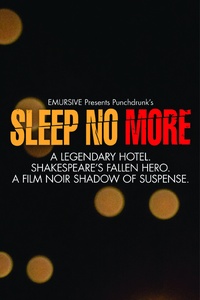摩伊賴
深度劇透,包括麥克白、男巫、門童完整情節(jié),和很多很多的秘密。附實用鏈接。
【深度劇透,包括麥克白、男巫、門童完整情節(jié),和很多很多的秘密。】
黑暗。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虛假的熒光一次次將你引向錯誤的方向,迷宮之中只有自己的手是可信的,可信嗎?我們不是已經(jīng)在人生的黑森林中迷路無數(shù)次了嗎?
一只腳踏進霧氣彌漫的靈薄獄。從沒見過這樣的靈薄獄:深紅燈光灑下舞臺,燭火忽明忽暗,金镲輕響,鋼琴流動,酒杯相擊發(fā)出一圈圈嗡鳴。觀察人們的臉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誰說臺下就不是戲呢?
我喝了一口酒。在我的近視眼中,一切都籠上了一層令人迷醉的暈影。這里是兩個世界的邊緣:下一步位面就會倒轉(zhuǎn),這一側(cè)是幽靈而那一側(cè)才是人間。微笑的服務(wù)生上臺來,像驅(qū)趕亡靈的天使一樣把人們一批批帶往帷幕。他牽著我的手,帶我們上電梯。電梯:一個永恒的夢魘,帶我們到世界之底。
第一幕 預(yù)言
我來得太遲了:最初的晚餐已經(jīng)是最后的晚餐。門徒們在長桌邊等待血腥的基督,他們動作緩慢,眼神交匯,光和霧和曖昧的笑在他們之間流動。麥克德夫和懷孕的夫人,國王鄧肯與王子馬爾康,性感女巫、光頭女巫,還有長著一雙勾魂眼睛的漂亮男巫。一聲吼叫,麥克白及夫人浴血走來,你不敢和男人對視,而女人無辜的嘴唇上沾滿了血。國王萬歲!眾人舉杯向主人致意,連先王鄧肯(活著?死人?)都慈愛地展開雙手,麥克白夫人高舉國王給她的項鏈,珍珠在寒氣中閃光。緩慢地,緩慢地,鬼魂上場了,班柯滿臉是血,凜然地掃視眾人,妖巫們擁他入座。這是正義的猶大,是赤裸裸的罪行和證據(jù),控訴他,控訴那個坐在主位上的人!麥克白痛苦地縮成一團。人們縱樂,然后縱欲,男男女女,活人和死人和妖魔,優(yōu)美地糾纏在一起。麥克白瑟縮著從桌前爬向夫人,爬向霧氣和黑暗深處。
宴席散了。一雙雙活人和幽靈的腳混雜在一起。奇怪的是我仍然覺得此處才是人間,我們從面具之后窺視著另一個冰冷的位面,鏡中世界。賓主消失于黑色的枝杈間,男巫伏下來,扛著樹木挪動。“鄧西嫩,”我說,命運已經(jīng)盯上了麥克白。
我眼睛四處亂轉(zhuǎn),腳步緊跟男巫。空氣中影影幢幢,不知是人是鬼,陰森森的霧氣四下漫過腳背。男巫站了起來,眼神迷離地向我走近。我動彈不得,他露出詢問的眼神,我點點頭。他輕柔地抓住我,手指撥開發(fā)絲,把一個吻印在面具外裸露的皮膚。“哈,”他一揮手,樹木神奇地點亮,如同圣誕降落在森林。
我暈暈乎乎地跟著他。他帶著一眾幽靈來到樓梯角,神圣的彩繪玻璃下。光線穿過玻璃十字,將天堂般的光暈罩在這個黑暗的角落,罩在這個也許來自地獄的生靈上。他在這里更衣,整理儀容,衣物落到另一個幸運的幽靈手上。他帶我們跑上狹窄的樓梯,來到二樓。這里就是所謂的麥金儂酒店了:富于希區(qū)柯克風(fēng)味,所有罪惡匯于一籠的壓縮空間。穿過禮賓,他來到擺著小沙發(fā)的大堂,和兩個女巫玩起了搶椅子游戲。光頭女巫現(xiàn)在長出了頭發(fā),變成了美艷女巫;她們穿著閃閃發(fā)光的曳地禮服,露出優(yōu)雅的長腿。他們歡笑,喝酒,親吻,爭奪,等待一個不速之客。
男人從濃霧中走來,三巫伸出修長的手臂迎接麥克白。把他拖到禮賓臺后,上演蠱惑兇暴的舞蹈。身體變成橋梁,變成光,糾纏著這個男人,麥克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心了,他無力地癱倒,嘴里卻發(fā)出無聲的大笑,命運,命運垂青著他!他大踏步走了,一張黑桃K釘在臺上。
空落落的大堂里只剩下男巫和門童。門童是個天真脆弱的胡子男人,他打開一個匣子,給男巫的眼角涂上粼粼波光,又被偷吻了指節(jié)。男巫再一次伸出邀請的手,把我摁進沙發(fā)。幽靈們紛紛入座,男巫登臺,唱一曲“My Funny Valentine”。歌聲幽怨,像是來自一個上世紀(jì)的鬼魂,波光就像是他的淚水,他看著未知的遠處,真的哽咽了起來。命運也會哭嗎?我頓悟它精巧的運行機制。就在此刻,不在此處,有多少掙扎、欲望和兇殺正在上演。為了不讓我們被他們絆倒,或者把他們絆倒,除了把我們牢牢栓在此處,命運別無他法。
(他們說在紐約,這兩個人從鏡中看見彼此。在“Moonlight Becomes You”中,門童和空氣共舞,穿上男巫的夾克,幻想自己成為另一個人。而男巫登臺,唱一首絕望的“Is That All There Is?”。男巫也曾是個男孩,直到他消失于空氣,而赫卡忒拒絕帶走門童的淚水。)
男巫哭起來。門童給他紙巾又離開。他緩慢地擦起眼睛,顫抖地捉住一個幽靈的手,握著它為自己擦眼淚。他吸吸鼻子,走向張大嘴等待的命運。
宴會廳。歡樂的爵士響起,人們雙雙對對開始舞蹈。 定睛一看,還不全是人:和王公貴族共舞的分別是美艷女巫、性感女巫,男巫纏著王子跳得開懷,只有老國王面前真的是人,是麥克白夫人。這組合總讓我覺得有些不對。不過他們跳得這么開心,華服旋轉(zhuǎn)成一個個漩渦,柔軟的肢體伸展到不可能的角度,一雙雙迷人的眼睛飄過,把暗流都埋藏進腳底。曲終人散,男巫沖上樓梯,捉迷藏般躲進一個小黑屋,天花板上掛滿了帶毛的野雞。他放下什么,沖我們笑笑。
三個電話亭,漆成不祥的鮮紅,召喚三巫前來,他們同調(diào)舞蹈。鈴聲響了起來,吸引幽靈如咬鉤的魚兒,美艷女巫抓起一個塞入幕后。男巫和門童舞蹈,又像在打斗,后者一次次摔入亭中,瞪著驚恐的眼睛喘氣。男巫頭也不回地走入深巷,幽靈們魚貫而出,留下一個心碎的人。瘋狂的三巫在此匯合,抓住一個幽靈啃向她裸露的肩膀,攥著她像是要獻上祭臺。狂奔,狂叫,狂笑,三巫合為一只野獸,在黑暗的走廊中狼奔豕突。性感女巫一聲尖叫,幾乎迎面和我撞上,“嘖嘖嘖,”她純潔的臉上露出哀憐,像哄小兔子一樣哄我,又森然露出獠牙,一爪子差點抓到臉上。他們跑了,我們緊緊跟上,沖進黑暗的祭祀場。
紅衣女人伸開雙臂等待。腥紅裙子鋪了滿地,像血。她有節(jié)奏地發(fā)出抽搐般的聲音,像一種可怕的鼓點。男巫伸出危險的手,領(lǐng)我走上高臺,我直挺挺地站著,懷疑要引頸受戮。燈光暗下來,不速之客終于到來,蘇格蘭國王跌跌撞撞地踏入洞穴,所有人顯出醉態(tài),因為罪惡太濃。“所有人”并不是人:燈光驟滅,你以為自己瞎了的一瞬間,又被閃爍的白光刺傷,在快速明滅的強光里你看到他們已經(jīng)不再是人了,女巫現(xiàn)出本性,紅女人化為魔神,男人從頭到腳被鮮血澆鑄,啊,從角落里鉆出了羊頭的撒旦,蹲在施洗臺上,一手持匕首,一手持一顆血淋淋的……心?撒旦在巡禮,女巫在尖叫,尖笑,狂放地舞蹈,舉起麥克白,舉起祭品,舉起他們自己,光頭女巫倒吊在空中狂笑。一個鮮血淋漓的死嬰被產(chǎn)了下來,抱到國王面前,滿頭是血的男人俯下身去……?我看不見也不想看見。
獻祭完成了。妖魔們癱坐成一堆。撒旦取下羊頭,果然是疲憊的男巫。麥克白從他們身邊滑走,他們直起身來,捏起一棵小小的玩具樹。
男巫抓起他的撒旦套裝離開。一瞬間他顯得那么累,那么年輕渺小。他走進浴室,沖去身上的血。幽靈們在昏暗的浴室門口窺視,我走開了,把他留給他自己。
不遠處就有燈光。格子窗后的小房間里有兩個男人,馬爾康和麥克達夫,我鉆進去他們就鎖上了門。昏黃的吊燈,作為唯一的光源,像利劍一樣在頭頂上擺動。燈光打向兩個人的眼睛,他們從眼窩的陰影中瞪視對方。精妙的舞蹈開始了,他們繞著椅子移步,忽而將另一人按上座椅,用強光審視他臉上的每一寸。麥克達夫是一個秀氣的中國男人,但也不見孱弱,他反手摁倒王子,用眼睛逼問后者。尖利的懷疑在目光間流動,照亮他們眼底的幽暗,在某個遠方掙扎的、他們共同的敵人麥克白。
我回到男巫身邊。他坐在地上,還沒有穿好襪子。幽靈們給他遞去衣物,他收拾好,帶我們走進深處。一個陰暗低矮的酒吧,綠色的臺球桌橫在中間,沒有人。男巫突然一陣抽搐,撲倒在桌上,身體不斷痙攣。他在桌上翻滾,踢打,抓撓,拱成詭異的曲線,動作間卻帶著一種奇怪的優(yōu)美。巨大的痛苦仿佛要從他身上破土而出,空間向他壓下,向他灌輸在另一個時間另一些主角身上發(fā)生的可怕的事,將它注入他的血管。他從噩夢中睜開眼睛,奔赴最后的晚餐。
第二幕 狂舞
麥克白在濃霧中尋找微光。他是個英國式的男人,有著英國式的痛苦。他瞪著發(fā)紅的眼睛,搖搖晃晃地穿過森林,等他清醒過來已到了二樓。一個提著手提箱的孕婦來了,那是麥克達夫夫人,她踩入大堂的花磚就像踩入陷阱。麥克白問候這個可憐的女人,女人用審慎的眼睛躲閃。男人猛然抓住她的胳膊,手提箱飛了出去。暴力的交響:力不能逮的壓制,生死一線的反撲,母獅般的女人竟有這樣的力量,數(shù)次掙脫又被抓回來,深深陷入花磚圖案的漩渦,漩渦的中心站著麥克白。
最后一擊。麥克白將孕婦的肚子撞上廊柱。
時間是錯亂的,我們回到了故事的出發(fā)點,還是說這里根本就沒有什么時間?麥克白和班柯凱旋歸來,在行李房洗去身上的血污。他們談笑風(fēng)生,然而那盆水端出來就是紅的。他在這兒殺過多少人,洗過多少次臉上的鮮血了?班柯仍不知道戰(zhàn)友即將變成什么樣的人,麥克白走后,他還將在這里跳一支沉思的舞。荒野中傳來女巫的笑聲,麥克白走向黑暗深處,妖魔們接納了他。黑桃K: 他的過去,他的欲望,他的命運。
還有一個人在等著他。麥克白回到臥室,在石盆中洗臉,穿睡裙的夫人從身后悄悄抱住他。命運激發(fā)的究竟是誰的野心?這是一場臥室中的角斗。親吻是危險的,蜜語和大笑也可能藏著埋伏。可是麥克白早已深陷漩渦之中,還是不免向欲望屈服。他們在錦繡大床上翻滾,在鋪滿水墨的墻上親吻,在狹小的空間中追逃,在箱子和柜子上跳躍舞動。難以相信,沉重的身體能在空氣中那么輕盈,腳尖劃出輕靈的曲線,這是精密計算的放縱,畫地為牢的自由。
夫人換上露背黑色晚禮服,命麥克白為自己拉上拉鏈。男人有些瑟縮。這時候我們才發(fā)現(xiàn),他就是舞場上少的那個人。
他站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心事重重地望著舞場。借他的目光,我們第一次看見迷情之下藏著什么戲碼。美艷女巫與班柯熱舞,性感女巫勾引麥克達夫,男巫更不允許王子的目光離開自己。于是沒有人看見麥克白夫人在國王懷中嬉笑,沒有人看到她給他下毒,除了一個人。
他很嫉妒。內(nèi)心深處,他又害怕。他的妻子是個什么樣的女人!他卻不能不被她吸引,跌下黑洞。男人把女人甩開,她卻不放他逃走。她用柔軟的嘴唇纏上他,用身體控訴他的懦弱。他把她狠狠摔上軟墻,她卻大笑。他在害怕什么?難道不是害怕自己心中燈光照不到的角落?美麗、黑暗、甜蜜,大笑著的身體,吸引著他又令他畏懼。他逃了,逃進黑暗的花園,陰森森得更像墓園,一座圣像無言地立在那里。麥克白在重重磚墻中橫沖直撞,甚至翻上墻頭,卻無處可逃。只有一處可去:國王的套房亮著燈光。
國王安眠著,這個老男人,睡臉那么天真安詳。鐘擺聲響得有些駭人。麥克白跨立在床榻邊,手撐在錦緞上,一動不動。昏黃的燈光只把這個角落照得大亮,鐘擺聲急促,催促著他。一群白色的幽靈睜著黑眼睛盯著他。麥克白有些笨拙地拿起一個枕頭,悶在國王臉上。鄧肯的手指無害地抽動,終于不動了;現(xiàn)在麥克白成了國王。
他洗手,突然滿手是血。他狂奔回房,幽靈旋風(fēng)般跟著他,門差點打在我臉上。麥克白在石盆中瘋狂洗手洗臉,紅色難以洗去,他快要崩潰了。夫人脫掉他染血的衣服幫他入浴,他縮在過小的盆里像一個孩子,不知道在不在哭。洗完澡,他踏出軟弱無力的腳,上床縮進毯子。夫人也到他身邊躺下。夫妻兩人瞪著充血的眼睛,直瞪瞪地盯著擠滿房間的幽靈,直到無眠之夜過去。
別再睡了!麥克白已經(jīng)謀殺了清白的睡眠,他只能去求助妖魔。跌跌撞撞,他走入它們的巢穴。它們獻祭了一個孩子,一個他本來會有的孩子,一個本來能有的未來。他吃掉了他自己。惡魔捏起一棵玩具樹,麥克白,它們摯愛的棋子。
鬼迷心竅,男人又沖進那墓室般的花園。圣母子像無聲地嘲笑著他。他頭痛欲裂,仿佛無形的巨爪捏著他的頭顱。仿佛頭生雙角。鬼使神差,他沖進一個酒館,中央一張鮮綠的臺球桌。僅剩的空間里擠滿了幽靈和兩個僵持的人。班柯難以置信地瞪著麥克白,慘白的光照著兩人繞桌周旋。暴力在空氣里過電,沿著一種瘋狂的韻律,他們開始推攘、撕扯、沖撞,將彼此狠狠摔打,班柯橫飛出去,重重撞上墻壁,這可不是軟墻啊!我的心和他的身體一樣揪了起來。班柯滑下墻,試圖作最后的抵抗,卻被麥克白抓住領(lǐng)子揍倒在地。燈光投射出麥克白的陰影,他已經(jīng)是一頭巨獸。他抄起什么向黑暗砸去。他起身,放低磚頭,黑血無中生有地從臉上流下。
沒人敢接近麥克白。他大步走進黝黑的走廊,領(lǐng)著一大群慘白的幽靈。他與夫人及其幽靈軍隊狹路相逢。他們發(fā)狠地擁抱,相擁轉(zhuǎn)過一個個幽暗的樓梯角,麥克白哭訴著,夫人緊緊摟住他,像摟著自己的孩子,親吻他的額頭,眉角,兩人發(fā)狂地啃咬,全然不顧團團圍住的幽靈的逼視,全然不顧一切,啃咬,弄得滿臉是血。
到了。男人張開雙臂,擁抱血色的霓虹燈。“伊樂園”:他的樂園,罪惡之園,他的純真墮落之地。
第三幕 命運
又是同樣的微笑。他們用同樣的姿態(tài)夢游,彷佛在互相取笑。美麗的人啊,眼睛里流動著可怕的東西。一聲痛喝,渾身是血的麥克白夫婦分開人群,就像分開血海。只有他們直直地注視彼此。目光穿過深陷漩渦的人們,或是人們組成的漩渦,直刺命運之底。班柯來了,帶著新鮮的血泊。狂歡開始了。麥克白逃不掉了。他笑著踏上高臺。燈光轉(zhuǎn)暗,復(fù)仇的天使給他慢慢套上絞索。他還在笑。活人死人和幽靈一齊注視著他。麥克白夫人,還有叫不出名字的女人,在臺下我的身邊。男巫隱在暗處。馬爾康和麥克達夫一左一右挾著他,就像人形的烈火。麥克白仍在狂笑,彷佛在等待一匹馬。他沒有等到。咳嗽,抓撓,青筋暴露,眼珠凸出,滿臉漲得紫紅。我們很害怕。兩只手冷然一推,一陣驚呼。
黑暗之上唯一的亮光,一具高大的尸體晃晃蕩蕩。
散場了。人們沉浸在夢境之中,無意識地匯成湍流。夫人在我身邊閃耀,我以為要被她帶走,直到男巫站起來。他四下環(huán)顧。他在找我。他來到我身邊,一手搭上我的肩膀,留下一個洗不掉的血手印。奇怪的是那是一只令人安心的有力的手,他帶我穿過人群,為我輕輕推開人流。燈光漸漸亮起,面前就是人間,幽靈們紛紛摘去面具。我扭過頭,看到他的臉籠罩著金色的光暈。星星點點在他的微笑上閃爍。我取下面具,幾乎發(fā)不出聲。”Thank you,” 我說。
摩伊拉鉆回了猩紅的帷幕。
劇終
2017.2.26白日夢回
我又回到了曼德利。幽靈在命運間走馬觀花。我走過霧氣彌漫的竹林,血跡斑斑的瘋?cè)嗽海幧哪沟亍T诨璋档男〗郑鞣狐S如古跡的偵探社、棋牌室、糖果屋。病號服如不詳?shù)钠鞄迷诶K索上飄蕩。解剖室的書桌上列滿了死者的名字。一個房間從頭到腳包裹著軟墊,一個房間如碑林般寫滿了粉筆字。但是,也不是沒有生機:王子和艾格尼絲,一個堅韌的中國女孩,爭執(zhí)又親吻。在紅繩圍起的結(jié)界中,(神似胡歌的)上海小老板和姑娘私定終身。動物標(biāo)本的包圍下,男人讀著幽靈的掌紋。向下,又撞見了漂亮的小哥哥,他是今夜遇到的第三個人。然而他的身邊粘滿了鬼魂,她們越來越大膽地侵入他的領(lǐng)地,他再也看不見我。我傷心地拐進一個小房間。一個鬼也沒有,門童正在寫信,戰(zhàn)戰(zhàn)兢兢。我盯著他,趴在他身邊。他突然瞪過來,目光穿過我的軀體,直射身后的空氣。他在害怕什么?
信寫好了,漂亮的花體字,筆跡顫栗。悉悉索索,他把信紙折成小船,用它盛起緩慢淌落的淚水。然后他吹氣,吹氣,小船落進空氣。我撿起來,不知所措。
Dear Madame, I cannot find what you seek. Please release me from our agreement. The forest is ever dark. Please, take my tears. I pray thy remember, The Porter
(如果女王收到了這封信,他就會消失在空氣中嗎?)
這門童,一派天真,老是微微撅著嘴,眼神脆弱。他和赫卡忒達成了什么協(xié)議?只見他纏著艾格尼絲,各種失敗的陰謀詭計,惡作劇不成還會把自己藏到簾子里。僅僅是一個孩子,掃除時跳跳踢踏舞,偷喝小酒,自得其樂。要總是這樣,他就不會哭了。他被太深地卷進了幾個女人的漩渦,毫無還手之力,被自己折磨,又厭惡著自己。男巫在那頭唱著"My Funny Valentine",門童在燈光這頭流淚。他在"Moonlight Becomes You"中與鏡子跳舞,幾乎吻上不知是誰的倒影。在電話亭里被男巫痛揍一頓,顫巍巍擦干眼淚,踏進下一個輪回。
我爬向神秘的上方。麥克白夫人被一大群幽靈簇擁而來,她腹部染血,縮在床上瑟瑟發(fā)抖。我則一眼盯上了她的小護士。小護士提著她的衣物去臥室放好,之后夫人將在此處跳起誘惑的舞蹈。護士帶著我們穿過整個病院,掠過懸滿符咒的桌子、塞滿病歷的柜子、淌血的浴室,走進陰暗的小房間。她看著自己的手,仿佛它不聽使喚;她捶著自己的膝,仿佛神經(jīng)快要癱瘓。毒素已經(jīng)漸漸滲進了她的身體。像男巫一樣,她在桌上桌下掙扎,與自己的身體角力。她用粉筆在墻上寫下無聲的吶喊,在黑暗里字跡難辨。抬頭,發(fā)現(xiàn)鋪天蓋地的中文,仿佛碑林。她拉起一個觀眾消失在洗衣房,白森森的衣服旗幟一樣飄蕩。她回到病房,藏起什么東西,撫摩床上攤成人形的病號服。枕頭邊塞著一張明信片,女性的秀麗筆跡:“近日我忙于學(xué)業(yè),無暇來看望你……”護士穿過逆光,在竹林中逡巡。她走到林中小屋,與黑人護士會面。靜靜地,靜靜地,她們用紅繩拉起了一方空間,她們面帶微笑,仿佛這是個網(wǎng)住幸福的結(jié)界。一對小情侶從霧中出現(xiàn),彼此凝視,新月般的眼神在黑暗中閃爍。他們起舞,敬拜天地,喝交杯酒,護士在一旁為他們見證。花繩還交纏在他們手上,風(fēng)起了,法海要來。紅線獵獵作響,疏忽全收回去。小夫妻慌忙逃離。
某個時刻,小護士的身后只有我一人。她溫柔又堅定地握住我的手,把我?guī)闲荨K难劬φ鎿从殖纬骸!澳愫退L得一模一樣!昨晚我夢見了你。我又夢見了曼德利莊園,月光照亮它的窗戶,海風(fēng)呼嘯,天空變成了沉郁的墨藍色。你想再回去一次嗎?”
我點點頭。她蒙住我的眼睛,帶我去未知幻境。巨大的、難以忘懷的曼德利……
“你知道,你再也回不去曼德利了。”
可愛的她目送我離開。我向她揮揮手。
這個孤寂的時刻之外,世界還在不停地滾動。我跟蹤一個黑衣男人,他夸張地跟蹤麥克達夫夫人,顯然不安好心,然而又偷偷幫她縫好了泰迪熊。我跟蹤馬爾康,他與班柯、麥克達夫打一場三人牌局,得到K者也許就是叛徒。他們突然發(fā)足狂奔,穿過不明所以的幽靈們,我發(fā)揮百米賽跑的速度窮追不舍,才看到另一場看不膩的審問。王子和麥克達夫握手言和,推出立滿小樹的棋盤,鄧西嫩的樹林要開始移動了。
命運沿著既定的軌道滾動,然而在最后的晚餐,男巫換成了其他人。我生氣又失望;后來才知道,小哥哥受傷了,門童替他上陣。那么,赫卡忒終究帶走了門童的淚水;僅此一次,男孩終于變成了他渴望的人。
在兩個世界的交界,女伶高唱一曲"Summertime"。我喝光一杯雞尾酒,待到燈火闌珊。莎劇去掉語言還剩什么?我想這是最好的答案。
2017.4.9 童謠之夜
她身上凝結(jié)了女性的美與恐怖。我在她面前就是一只待宰羔羊。這里也是曼德利,然而空無一人,只有鬼魂。她登臺演唱,紅色長裙在聚光燈下就像酒精的火焰。曲調(diào)急轉(zhuǎn)直下,嗓音變成男聲,她哽咽起來,又笑了,用一個小瓶收集自己的淚水。
臺下觀眾還是巋然不動,笑瞇瞇地等到一曲“My Funny Valentine”結(jié)束。戀人們依偎在一起。狡猾的仆人隱在角落。兩層樓下,男巫的演唱也快結(jié)束了,他是否只是赫卡忒的木偶?歌聲嘲笑著一對對可悲的戀人,包括他自己。
早已準(zhǔn)備好的雄黃酒,給白娘子喝。臺上兩個面目模糊的男人跳著機械舞。仆人不斷給白娘子倒酒,被她偷偷倒掉。巫神拿起她的羽毛扇子,伸出帶著絲絨手套的手。她的閨房幽深,梳妝具列在臺上。她對鏡,又看我,開始對我耳語。“從前有一個小男孩,在森林中……”
她把我拖進密室中的密室。一片漆黑,手被按到墻上,摸到密匝匝的藤蔓。“小男孩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位老奶奶,要他幫忙找自己的結(jié)婚戒指。小男孩找遍了整個森林也沒有找到,除了一陣陣笑聲,林中什么也不剩。他坐下來哭呀,哭呀——淚水嗆到了他的喉嚨。”
她蹲下來哭,聲音凄厲。撫過我的臉頰,像要偷走我的淚水。
“找回我的戒指!你知道它在哪里。”
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它在哪里?茫茫五層樓,無數(shù)個幽暗的房間,大海撈針地找一枚戒指。“簡直像尋找圣杯。”
我在種滿草藥、寫滿符文的房間里尋找。在小小的墳頭撥開灰燼。在當(dāng)鋪里翻箱倒柜,箱子里裝著蛇蛻的皮。竹林之中,大眼睛的小護士請我喝茶。茶是冷的,伯爵茶。講一個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小男孩,他孤身一人 他上月亮,月亮是一截枯木 他上太陽,太陽是一朵枯萎的向日葵 他伸手去夠星星,星星變成了一群螢火蟲 他回到人間,人間是個倒翻的尿盆
該走了。去陰暗潮濕的醫(yī)院,打開一扇扇門。娃娃屋有著罕見的溫馨,另一位護士哄我睡下,放下床簾,鉆進來給我講故事。故事越來越可怕了。“從前……”
有一個孤單的人,他的頭是個南瓜, 眼睛是兩截蠟燭, 身體是一段木頭。 他很痛苦,用手捶碎了南瓜頭 卻死不了。 他必須找斧子砍碎木頭, 找小鳥啄碎南瓜, 找小男孩吹滅蠟燭, 找齊這三樣寶物,才能死成。
“快離開這里,”她說。
我又回到了赫卡忒身邊,她是一塊磁石,吸引形形色色的人。男人前來,在空無一人之地與她接吻。女巫拒不從命,卻被逼穿上舞鞋。艾格尼絲涂上口紅,變成痛苦的木偶,被搶走了吊墜。紅衣女郎只是笑,只是笑,在我面具上留下猩紅的唇印。
她開始用餐,吃帶血的肝臟。笑,用銀閃閃的刀子晃幽靈的眼睛。突然噎著,表情痛苦,吐出一枚戒指。
來,她招手。擦干凈,把戒指戴上我的無名指。
這就是她丟失的戒指嗎?丟失的又怎么可能又在她嘴里?銅戒指在我手上閃耀,我卻不敢再問,奔赴可憐的戀人們。
再看一次。命運的木偶翩翩起舞,喝交杯酒,私定終身。來到巫神的酒吧,攜手聽厄運唱歌。躲無可躲,灌下致命的酒,踉蹌翻騰,口中咳出黑血。架入醫(yī)院,門砰地在男人面前關(guān)上,他瘋狂捶門,撞門,四處尋找鑰匙,看見一頁頁紙片上剪滿蛇形。在林間和巷中發(fā)足狂奔,誤入祭祀,頭痛欲裂。頭頂上方同樣喧聲震天,他破門而入,撞見被單下扭動著巨獸,女人緩緩升起,口吐黑血,仿佛黑蛇。
男人昏死過去。
白蛇從病院逃離,跌跌撞撞,傷心欲絕。她在鋪著十字架的毛巾中央發(fā)狂洗臉。她沖進溫室,脫下舞鞋,攀爬上天。蛇行于天空,采下草藥。在下一個輪回中,她才能喚醒心愛的男人。
在這個輪回中,她牽著我的手,奔向結(jié)局。
麥克白在空中掙扎,她的手也越收越緊,最后緊箍住我。麥克白吊死,她驟然放手。我們奔向人間,像兩個同病相憐的人一樣擁抱。
觀劇指南
Spoiler-Free-User-Friendly-Guide to SNM(墻外):極其實用的新手指南。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Tumblr #Sleep No More: 聚集了很多狂熱粉絲,他們致力于每一場的對比研究 Sleep No More Wiki: 如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