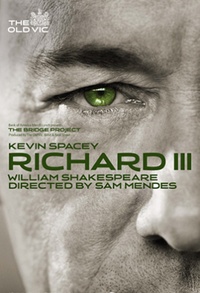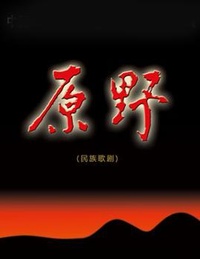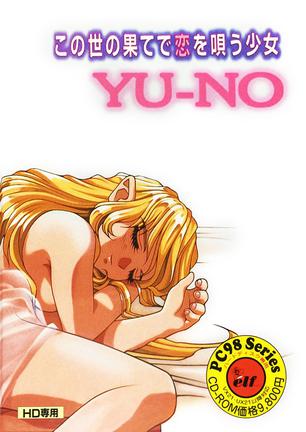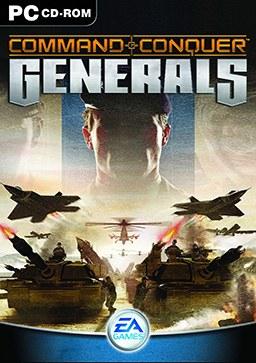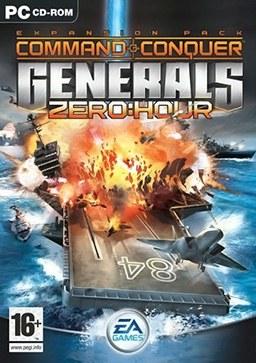麥克默多的浮冰的評論 · · · · · · · · · · ( 評論25 )
- 陶喆的Stupid Love Songs:一場私密而五彩斑斕的流行音樂尋根
-

-
麥克默多的浮冰
(保持愚蠢,巴托比。)
評論:
STUPID POP SONGS
在嗓音條件與旋律創作能力不復當年、而編曲功力和制作經驗越老越妖的情況下,陶喆還能交給今天的華語樂壇一份怎樣的答卷?循環十幾遍后終于意識到,這就是一整張全部以Pop為基底、但曲風足夠包羅萬象的現代流行音... (2回應)
- 一場徹頭徹尾的造夢之旅
-

-
麥克默多的浮冰
(保持愚蠢,巴托比。)
評論: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走出影院的那一瞬間就已經確信,無論視效還是敘事層面,在我心中《縱橫宇宙》已經全面超越了第一部,盡管第一次聽到《Sunflower》的那個瞬間永遠無法替代。可能是“電影已死”之后,迄今最為精彩的半部“電影”,...
麥克默多的浮冰的移動應用 · · · · · · ( 用過30 )
“某些人的光榮或者優點在于寫得好。
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寫。”
“是否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虛構人物,
生活授權給我們,自己把自己寫出來?”
前一句話出自恩里克·比拉-馬塔斯《巴托比癥候群》的扉頁,意在殘酷地點明這一事實: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不寫”或者“我寧可不”,已經是唯一能夠把握的美德。
后一句話出自詹姆斯·伍德《小說機杼》(上河卓遠版)第80頁,伍德談到“薩拉馬戈那部偉大的小說”《里卡多·雷耶斯逝世那年》,薩拉馬戈借佩索阿著名的異名對同一個人物進行雙重虛構,“里卡多·雷耶斯”竟然隱約感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虛假的,當他在世界邊緣失落地自省時。當后現代小說家們自視為虛假人物背后的上帝時——薩拉馬戈卻驟然拋出這個截然相反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篤定自己一定存在?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無論如何交換字句擺放的位置,都注定要達成某種恐怖的平方。
“知識可以傳授,但智慧不能。”
“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
相較之下,這是兩個流傳甚廣的金句。前一句話出自赫爾曼·黑塞的“療愈”小說《悉達多》,后一句出自聞一多最著名的豆腐塊詩歌《死水》。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并交換字句擺放的位置(此處的交換是一種必要),大概就是這樣的效果:
斜眼看世界(鼻炎),諷眼看自己(抉心)。
“友鄰是福”,同時也是無形的壓力,是無數雙智慧且過度智慧、來回審視的探照燈,又總自覺感到自己的無知,于是巴托比癥晚期嚴重發作,只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選擇閉嘴,瑟瑟守好自己極私人的一畝三分地。對一切保持懷疑和疏離的同時也竟沉淪和迷醉,又在此基礎上鞭笞起自己這“十足的臭蟲”,以獲得“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還有兩句話,是我在盡力掙扎著顯示自己依舊存在時,量身定制的雞湯:
時刻銘記“品味和格調”一文不值,極端尊敬文藝創作者而鄙夷自己這樣的文藝消費者;道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用于自律,有些話只有反求諸己時才不是心靈雞湯。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繼續祭出魯迅的金句:“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寫作是一種示弱,刺猬將自己柔軟的肚皮,坦露給世界上所有的箭鏃。寫得越多(宛如康拉德的小說),越像是在竭力虛構,越無法確證自己的存在。
伍德緊接著在第81頁這樣寫道:
這本小說的問題,以及絕大多數薩拉馬戈作品的問題,并非瑣碎的“元小說”游戲“里卡多·雷耶斯是否存在”。它尖銳得多些:“如果拒絕同任何人發生聯系,我們是否還存在?”
也許這就是豆瓣“存在”的“意義”。
自勉自噬。(20230913)
一個書影音的精神自留地。所有短評長評照片日記都很難真正代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自己,而只能被視為刻舟求劍的故事里長眠于河底而永久凝結為時間和空間的琥珀,順流而下攜帶著的只有一部分殘存于流動不居的模糊記憶。
我愛故我在。
(晚安Khalil。)
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寫。”
“是否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虛構人物,
生活授權給我們,自己把自己寫出來?”
前一句話出自恩里克·比拉-馬塔斯《巴托比癥候群》的扉頁,意在殘酷地點明這一事實: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不寫”或者“我寧可不”,已經是唯一能夠把握的美德。
后一句話出自詹姆斯·伍德《小說機杼》(上河卓遠版)第80頁,伍德談到“薩拉馬戈那部偉大的小說”《里卡多·雷耶斯逝世那年》,薩拉馬戈借佩索阿著名的異名對同一個人物進行雙重虛構,“里卡多·雷耶斯”竟然隱約感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虛假的,當他在世界邊緣失落地自省時。當后現代小說家們自視為虛假人物背后的上帝時——薩拉馬戈卻驟然拋出這個截然相反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篤定自己一定存在?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無論如何交換字句擺放的位置,都注定要達成某種恐怖的平方。
“知識可以傳授,但智慧不能。”
“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
相較之下,這是兩個流傳甚廣的金句。前一句話出自赫爾曼·黑塞的“療愈”小說《悉達多》,后一句出自聞一多最著名的豆腐塊詩歌《死水》。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并交換字句擺放的位置(此處的交換是一種必要),大概就是這樣的效果:
斜眼看世界(鼻炎),諷眼看自己(抉心)。
“友鄰是福”,同時也是無形的壓力,是無數雙智慧且過度智慧、來回審視的探照燈,又總自覺感到自己的無知,于是巴托比癥晚期嚴重發作,只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選擇閉嘴,瑟瑟守好自己極私人的一畝三分地。對一切保持懷疑和疏離的同時也竟沉淪和迷醉,又在此基礎上鞭笞起自己這“十足的臭蟲”,以獲得“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還有兩句話,是我在盡力掙扎著顯示自己依舊存在時,量身定制的雞湯:
時刻銘記“品味和格調”一文不值,極端尊敬文藝創作者而鄙夷自己這樣的文藝消費者;道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用于自律,有些話只有反求諸己時才不是心靈雞湯。
而當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繼續祭出魯迅的金句:“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寫作是一種示弱,刺猬將自己柔軟的肚皮,坦露給世界上所有的箭鏃。寫得越多(宛如康拉德的小說),越像是在竭力虛構,越無法確證自己的存在。
伍德緊接著在第81頁這樣寫道:
這本小說的問題,以及絕大多數薩拉馬戈作品的問題,并非瑣碎的“元小說”游戲“里卡多·雷耶斯是否存在”。它尖銳得多些:“如果拒絕同任何人發生聯系,我們是否還存在?”
也許這就是豆瓣“存在”的“意義”。
自勉自噬。(20230913)
一個書影音的精神自留地。所有短評長評照片日記都很難真正代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自己,而只能被視為刻舟求劍的故事里長眠于河底而永久凝結為時間和空間的琥珀,順流而下攜帶著的只有一部分殘存于流動不居的模糊記憶。
我愛故我在。
(晚安Khalil。)
訂閱麥克默多的浮冰的收藏:
feed: rss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