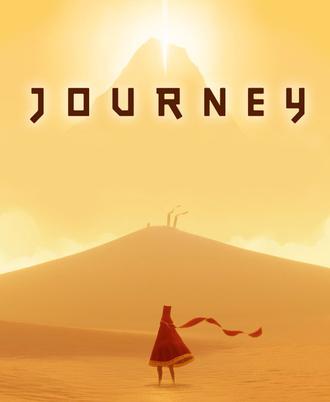《旅者陳星漢》——“禪派游戲”設計師陳星漢本人最喜歡的專訪
發表于知乎專欄【初心咖啡店】
【By】 SimonParkin 【譯】Edwin
翻譯自Eurogamer對陳星漢的專訪 原文題目:《風之旅人》的創意總監追求成為全世界最好的游戲制造者
“奧古斯汀說過……”
陳星漢放下了他的漢堡,給了我一個溫暖但堅定的凝視。這位《花》和《風之旅人》的設計者引用了三世紀的一位神學家作為談論 “網上茗茶”(此處應為指代陳星漢所開發的游戲)的切入點。“奧古斯汀寫到:‘人們會為了尋求驚奇冒險攀登至高山之巔,會為了沉浸在驚奇中而佇立凝視海洋的遼闊。但是盡管每個人都是個奇跡,他們在街道上與他人擦肩而過時卻毫無感覺。沒人能看到他人的神奇之處,真是奇怪。’”
陳略微吸了口氣,“視頻游戲里如果你在網上隨機遇到一個玩家,將會是段不好的體驗,”他說,“你認為對方會是個混蛋,對吧?”
我點了點頭,仍然沉浸在奧古斯汀以及從一開始坐下和這位工作室的中國游戲開發者談話就感受到的神奇當中。
“但是聽著:我們沒人生下來就是個混蛋,”他說。“我相信經常并不是玩家真的是個混蛋。是游戲的設計者湯他們變成了混蛋。如果你每天都在殺死其它人,怎么可能成為一個友善的人呢?所有的主機游戲都是關于互相殺戮,或者同時殺死對方……你沒看到嗎?是我們的游戲讓我們變成了混蛋。”
在他的最新游戲《風之旅人》正式發布的前幾天,陳和我在離舊金山莫斯克尼中心幾百米遠的一家熱鬧的咖啡館里共進了午餐。去游戲開發者大會(GDC)中途停下來買食物的人們響亮的談話聲填滿了這里。
陳說話用的是計算機極客的方式:安靜而又睿智,有些人會認為這是神經質地傲慢。但他的語言像一個虔誠的傳教者一樣,為了呼吁游戲設計者們創造更好系統從而可能創造出一個更好的線上世界,而向他們傳遞人文主義的精神。
在我們的午餐談話中不止一次我在胳膊上摸到了雞皮疙瘩。陳,就像一個20世紀60年代的音樂記者說的那樣,有靈魂。但是這顆心從何而來?將這位設計者引領至此的又是怎樣的旅途呢?
【歷險的召喚】
14歲的時候,坐在上海的一個小公寓的床邊的陳星漢放下了手柄哭了出來。
“在我可以讀什么或者看什么上面,我的父母嚴格得難以置信,”他告訴我。“我只能接觸到有限的小說、電視和電影,這部游戲是第一個讓我感動到流淚的媒介。那是我第一次哭,如此深入而強烈。我從未有過如此的經歷。”
《仙劍奇俠傳》在中國RPG史上就像《最終幻想7》一樣。它關于愛和失去的劇情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現在再去回想,我發現這個游戲膚淺而又老套,”他說。“但是這是第一次有媒介給了我這樣的沖擊,讓我愛上了它。”
陳通過這些眼淚得到了宣泄(這一話題在我們的對話中他提到了多次),擦干眼淚,他感受到了一種讓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的安寧。“我發現我自己再問:我想過哪一種生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我為什么在這里?在那之后我感到自己成為了更好的人”
“然后我開始審視未來,我決定我要將我的畢生用于幫助他人體驗我剛剛感受到的經歷。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將會通過游戲實現,但是我知道這將通過某種東西實現。”
在他生命的前22年,陳沒有離開過上海。
他的童年充滿了限制:現實的,社交的和雙親的。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讓他沒有兄弟姐妹,這個國家沒有來維持退休計劃的省或者公司,撫養雙親的全部責任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為了(畢業后)獲取良好的收入,在學校取得成功的壓力巨大。對于陳這樣重點班的有天賦和才華的年輕學生來說則更為之甚。“這是個冷酷無情的系統,”他告訴我。“每個學期班上最后三名的孩子將會被淘汰。我在的是這樣的一個精英班級,所以如果被淘汰進入了一個‘普通’班里別人會把你稱為失敗者。”
限制,競爭,排名:陳成長過程中的所有的社會系統也都在大多數視頻游戲中盛行。奇怪的是他的創作中這些都失蹤了。我向他詢問,是否是這些成長過程中這些現實的和心理的限制使他遠離了競爭的、基于任務的游戲。畢竟《花》被設定在了鄉村間,章節之間點綴著呈現城市公寓中枯萎的花的短鏡頭,或許是因為在上海的時候夢寐以求的自由,讓他的最新作品,《風之旅人》,成為了一個完全沒有多人競賽內容的游戲。
直到現在為止,陳一直用著溫和的語氣交談,停下來等待每個回應,偶爾會把問題拋回給我。但看得出這個問題讓他變得煩惱起來。“我是個競爭者,”他說。“我玩并且愛玩競爭的游戲。你知道,我在高中的時候是一個格斗游戲的冠軍。我在大學的時候是《星際爭霸》的冠軍。我也有在玩DOTA。我喜歡贏。我熱愛勝利。至于做游戲,并不是我愛和平的游戲。我做這種游戲,也是因為我喜歡贏。對我來說,一個人的偉大與否要看他們對社會做的貢獻。游戲產業并不需要再多一個射擊游戲,它需要帶來啟發的東西。
我向他詢問,是不是他的競爭性格意味著他希望能在游戲設計上“取勝”,以及是否他去探索一個較少被探索的領域也是為了提高這一幾率。
“是的,”他微笑著回答。“對我來說痛恨教育系統也毫無用處,我在教育系統中存活了下來。”
【試煉之路】
我們在水牛城燒烤餐廳吃飯,這也是事先計劃好的。陳告訴我這是他八年之前第一次去GDC時吃第一頓飯的地方,所以他帶我來這里。被14歲那年《仙劍奇俠傳》帶來的改變一生的體驗影響,他決定要成為一名動畫導演,制作像吉卜力工作室那樣風格的電影。
但時在大學期間,他的一些朋友決定要做一個游戲,找來陳制作模型和動畫。“最后我們做了三個游戲,”他說。“他們都是復刻版,當然,但是都是很好的游戲!其中一個是《暗黑破壞神》的復刻版,另一個是像《風之杖》那樣的全3D版的《塞爾達》。
“很有野心,”我說。
“我知道,但時我們完全把它擱置了。”從大學畢業之后,陳進入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電影,很大程度上忘掉了制作游戲的經理。但是當他的講師們發現他在寫代碼方面的能力(計算機科學方面的特長并非出于偶然,他在大學期間學習了這一課程)他被分配進了電影學院的游戲項目中。
陳并沒有和這一決定對抗,而是接受了它,他性格中競爭的一面意識到游戲為他提供了一個競技場,在其中他有可能會比在好萊塢做出更大的成就。
“電影是很成熟(的行業);對于每個想要的每種感受都有對應的類型,”他說。“不論你是什么年齡,類型,國籍和心情總能找到適合你的。但是游戲……你找得到驚悚片,恐怖片,動作片,以及體育勵志片。但時沒有愛情片,沒有劇情片,沒有紀錄片,也沒有生活中的思想實驗。這些都是人們想要在生活中擁有的基本情感,但時在游戲里都沒有。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長大了就不再玩游戲;他們想要體驗到這些但是游戲并沒有提供。
在陳看來,大多數游戲只提供了年輕人感新區的體驗類型,而在人生后期將學習和掌握的相對較少觸及。
“游戲,本質上是我們學習一些東西的工具,”他解釋道。“當我們還是在操場上玩樂的孩子的時候,我們了解了我們自己的身體,并且發現了和其他孩子相處的基本方式。但時隨著你長大,進入少年時期,你參與到了像是籃球或者足球這樣的游戲中。你學到了團隊作業。但是你很少見到35歲以上的人還在玩游戲。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學會了并且精通了這些技能。你看那些年長的人,他們玩撲克。撲克是一個關于欺騙、計算和操縱的游戲;這些是人生后期需要掌握的游泳的技能。高爾夫球是另一個例子。相對于社會鏈接,高爾夫并不是和運動本身很相關。它鼓勵你和別人一起進行互動。”
“我西歐昂新只有三種方式能夠創造對成年人有價值的游戲。你可以從知性方面,讓作品揭示出你之前沒有注意到的關于世界的新的角度。我所見的最接近這一點的是《傳送門》。第二種方法是從情感上:讓他人感動。你可以非常容易地讓孩子感動,但是讓成年人感動要難得多,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成年人感動,就是創造某種和他們的生活特別相關的東西,或者創造某種東西讓它如此的真實以至于可以帶來力量。為了達到這些高度,你需要得到精神凈化。這樣一個成年人在經歷了自身的強烈感情之后,才會開始尋找他自己人生的意義。因此我認為我可以為我身邊的人做游戲。第三種,也是最后一種方法是創造一個社交環境,在其中可以由他人帶來智力上的或者情感上的刺激。只有這三種方法。”
因此陳開始在影視學院學習游戲設計,然后有一年的春天,USC派他去GDC。“當時我還以為每個美國孩子都是像約翰·卡馬克那樣的編程天才,”他笑著說。
“但我為了了解學生做的游戲去了IGF區,然后我恨不得說‘這些游戲都是垃圾!’嗯,我在大學期間做的游戲比這些要好得多。當時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跟他說:‘咱們來做游戲吧,我們可以做得比這要好。’”
當陳和他的朋友回到USC他們就著手做一個名為《云》的游戲,一個被他戲稱為“同盟模擬”的飛行游戲。所有的孩子都夢想著要飛翔,但時對于陳,因為受到了如此多的限制,這一渴望可能比大多數孩子都要強烈。他們兩個把這個游戲放在了網上供免費下載,很快陳就開始收到關于他的作品的電子郵件。
“我收到在日本的人發來的消息,生成他們在玩的時候哭了。有人甚至稱我是個美麗的人,因為我做了這個游戲。所以我沉下來思考:是做什么正確的呢?這個游戲和其它游戲的區別在哪里?我能想到的唯一區別就是這個游戲讓你感受不同。在那一瞬間我認識到這就是我人生的呼喚。我可以去改變人們對游戲的看法,而不是成為一個電影或者動畫導演。我甚至要說我覺得我有責任去這么做。”
【追尋】
2006年,陳第一次被拒絕參與獨立游戲節(IGF)兩年以后,他的游戲《云》在這一活動中的學生展示競賽中勝出。盡管如此,設計者對他的作品卻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游戲,因為它的操作“不直觀”。我問他如果是這樣的話,到底是什么讓玩家產生了共鳴,進而給這款游戲帶來了如此多的關注。“我認為是單純和孤獨,以及同時感受到的自由和傷感,”他答道。
迄今為止,孤立和超然一直是陳的作品主題。我想知道為什么他著迷于此呢?
“我想是因為我們是創造者,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容易變得孤獨,”他說。“藝術家們渴望被聯系在一起。我們想要感到被理解,想要你感到我們發出的聲音被傾聽。事實上我受到了500封關于《花》的電郵……我覺得我說了,有人聽到了。而且因為作為人類,我們通常是孤獨的,所以得到他人接納的渴望才會如此強烈。當人們體驗到同樣的孤獨感時,他們直接的反應是跟人接觸和建立聯系。我能想象到任何一個在創造什么的人正在尋求與他人的連接。”
他直勾勾地看向我:“比如你作為一個記者,你在尋找能夠聽見你的聲音的人,不是嗎?”我咬了一口漢堡。
這種和他人體驗同樣的孤獨感的意境成為了陳最新的游戲核心內容——PSN下載游戲《風之旅人》,一個精確地詮釋了設計者為全新種類的感情體驗創造空間這一愿望的游戲。
但是這個游戲時長兩三小時的游戲經歷了三年的開發(比原計劃多出一年),與原項目相去甚遠。在原始項目中,陳希望能夠喚起的微妙感情難以表現出來。“《風之旅人》本是一個四人游戲,”他解釋道。“四個人提供了許多額外的社交要素。它更加有趣。但是我癡迷于創造兩個人之間獨一無二的連接,而我發現額外多出來的兩個人將破壞這一連接。創作一個有意義的四人游戲比雙人游戲要難得多。”
“我們想創作《風之旅人》的原因,除了最后到達情感宣泄的時刻,還有希望能在兩個人之間創建真實的鏈接。我這么做是因為大多數人現在都說:社交游戲很火爆。但是沒有其他的游戲是真正在兩個人的情感交流的層面上達到社會化的。在幾乎所有的游戲里,兩個玩家之間僅有的交流是子彈和數字。在Facebook上更多的是數字,在PC和主機上更多的則是子彈。
“所以作為一個設計者,我想看看我是否能夠創造情感交流。起初我們搭建了所有典型的協作機制。拯救他人,治療,一起開一扇門,諸如‘你站在這里,我站在那里,然后什么東西開啟了……’然后我意識到這些仍然是機械的交流。為了真正的交流感受,你需要讓玩家為交流情緒感受做好準備。”
陳向四周看了看,轉向了GDC會議中心的方向。
“我將會解釋,”他說。“當我在會議中心漫步時我在思考我需要在何時到達何處。我處于一種任務解決模式。我對社交并沒有興趣。在大多數視頻游戲中也正是如此。大多數的多玩家體驗是關于解決任務的。但時如果玩家在任務解決模式中,他們并沒有在交換情感連接的正確思維框架里。所以為了讓他們準備好,我們不得不移除掉關于任務的所有內容:從《風之旅人》中移除掉所有的任務和謎題。這樣一來,玩家將更可能會為進行社交做好準備。”
他停頓了下。“然后我們努力讓你感覺到孤獨。在這個精神層面上,玩家開始尋求連接,或者接近與他們相像的某人或某物。這就是我們做的。我們除去所有的東西,為的是創造一個玩家可以在其中交流感情的環境。”
我指出,陳像是要通過去掉這些機制來嘗試著復現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出現的社交互動。但是沒有必要說什么或者盡量對著什么談話,這是一個有趣的嘗試。這有意義嗎?
“圣奧古斯汀曾經說過,”
陳星漢放下了他的漢堡,溫暖而又堅定地注視著我。
“奧古斯汀說:‘人們會為了尋求驚奇冒險攀登至高山之巔,會為了沉浸在驚奇中而佇立凝視海洋的遼闊。但是盡管每個人都是個奇跡,他們在街道上與他人擦肩而過時卻毫無感覺。沒人能看到他人的神奇之處,真是奇怪。’
“在視頻游戲里,有這樣一個假設:如果你隨機在網上遇到了一個玩家,將會是一段不良的體驗。你認為他們會成為混蛋,是吧?但聽好了:我們沒有人生來就是混蛋。我相信一般來說并不是玩家真的是個混蛋。是游戲設計師讓他們變成了混蛋。如果你把每一天都花在互相殺戮上,你又怎么能成為一個和善的人呢?所有對的主機游戲都是關于互相殺戮,或者一起殺死其他人……我們的游戲讓我們變成了混蛋。”
“或者是關于把其他的玩家變成一種資源,用他們來開門之類的?”我插嘴道。
“是的,”他說。“是系統讓玩家變得殘忍,不是玩家自己。所以如果我使用了正確的系統,玩家就是人類,他們的人性就會被發掘出來。我想要給游戲帶來人的價值,并且改變玩家(在網上隨機遇到其他玩家將會是不好的體驗)的假設。”
陳把手伸進口袋中掏出了他的iPhone。“我要給你看一點東西,”他說。
“昨天《風之旅人》在PS Plus(索尼的收費會員服務,付費會員可以享受到提前得到新發布的游戲等特權)訂閱欄里上架了。幾個小時之后,一些玩家在游戲論壇里發起了名為‘旅途的歉意’的帖子。”
“那是什么?”我問。
“自己讀下把,”他說著把手機遞給了我。
這是一連串玩家向他們在游戲中的旅途遇到的匿名玩家的感謝和道歉。
?今晚我真心感激你的幫助。你在我沒有獲取飛行技能的時候如此地耐心。
?我很抱歉當那東西找上我們的時候我因為恐懼藏在了石頭后面。它讓我有點措手不及。
?致我在第五區域里的朋友。我從沒有想過要離開你,只是在跳躍的時候被猛地吹跑了。我想你。抱歉。
?致我所有一起游戲的人:感謝你們從未離我而去。
在我閱讀的時候,陳向我微微一笑。
“我起雞皮疙瘩了,”我說。
【與女神相會】
在我們努力清空我們的盤子的時候,我們的對話稍作停頓。食物已經涼了。
過了一會陳又開始講到:“在《風之旅人》的開發過程中,我有一次痛恨我自己。”
“怎么回事?”我抬起頭問。
“我們做了一個原型,玩家可以互相幫助完成任務。我們的一位開發者建議說加入一股強烈的風讓玩家只能通過互相推動來通過它會很有意思。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任何碰撞判定,所以我們加入了碰撞來實現這一機制。但時你知道發生了什么嗎?當團隊可以在游戲里面互相推來推去的時候,他們做的就只有把對方推進死亡的深淵。及時我們都知道這個游戲是關于積極的事情關于人性的,每個人都只是想要殺死他人。我自己也無法抗拒這么做的沖動。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對我的團隊成員和我自己相當傷心失望。“
“然后我遇到了一個兒童心理學家,我告訴了她游戲中的困局。她跟我說:‘哦,你的玩家們只是又變回了孩子而已。’”
“她是什么意思呢?”我問。
“我問了同樣的事情。她說:‘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他們是沒有道德觀念的。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好壞。所以他們嘗試那些給予了他們最強烈的反饋的行動。’”
“我不明白,”我說。
陳用叉子敲打桌面。鄰桌的一對情侶轉過頭來,不知道是關心還是惱怒。
“一個孩子會這么做,是吧?”他說。“你告訴他們聽,但時他們不僅不停,反而弄得更吵。對于孩子來說,這給了他們最強的反饋和注意。這位心理學家告訴我這就像玩家第一次進入虛擬世界一樣。他們就像孩子一樣。他們不知道規則,所以他們進行那些給予了他們最強烈的反饋的行動。她說:‘讓孩子停止做某件你不想讓他們做的事情的最好方法是你什么反饋都不給他們。’”
“問題在于,每個人都在尋求最大程度的反饋。如果你把某個人推進深淵,反饋是巨大的:另一個人死了,有動畫,聲音,社交壓力和讓她復活的機會。這些事情合在一起讓把另一個玩家推進深淵比只是把他們推進風里更令人滿意。“
“我明白了,”我說。陳停止敲打桌子,那對情侶又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回了漢堡。“那么當你去掉所有的碰撞判定后發生了什么?”
“玩家開始尋找獲取更多反饋的其它方法。互相幫助提供了最多的反饋所以他們改去這么做了。真神奇。”
【英雄的旅程】
我們的會面快要結束了。GDC的樂趣在于沒有圍繞在設計師周圍的公關人士,讓像我們今天這樣自由而不受限制的對話成為可能,但仍會因為出席會議環節而讓我們沒有無限的時間。我們吃光了食物,開始漫步走回會議中心。但我仍然對陳將游戲比作電影的觀點感興趣,對于一個像他那樣的游戲設計者這不是一個常見的比喻方式。他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如此緊密嗎?可能有某些主題視頻游戲不善于表達,或者有某些情感視頻游戲不善于反映。
“不。游戲時一種可以將電影的所有元素與互動化的設計相組合的媒體,”他堅定地說。“對于所有的意義和目的,游戲都會是比電影更適合(的媒體)。但時事實上,游戲現在仍然是電影產業的一個分支。這是個悲劇。我看到了如此多的潛力。我感覺到我在這里有如此多可以做的事情。”
陳性格中競爭性的一面又顯露了出來。
“所以我們嘗試著去做的是去引領情感因素。如果整個游戲行業都專注在興奮和腎上腺素沖擊上……嗯,那我將關注和平,或者愛。這樣我們可以拓展對于游戲可以是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的認知。這就是我為什么做游戲。這就是我為什么踏上了這一旅程。”
歡迎掃描二維碼訂閱【初心咖啡店】微信公眾號,第一時間獲得文章推送。

【By】 SimonParkin 【譯】Edwin
翻譯自Eurogamer對陳星漢的專訪 原文題目:《風之旅人》的創意總監追求成為全世界最好的游戲制造者
“奧古斯汀說過……”
陳星漢放下了他的漢堡,給了我一個溫暖但堅定的凝視。這位《花》和《風之旅人》的設計者引用了三世紀的一位神學家作為談論 “網上茗茶”(此處應為指代陳星漢所開發的游戲)的切入點。“奧古斯汀寫到:‘人們會為了尋求驚奇冒險攀登至高山之巔,會為了沉浸在驚奇中而佇立凝視海洋的遼闊。但是盡管每個人都是個奇跡,他們在街道上與他人擦肩而過時卻毫無感覺。沒人能看到他人的神奇之處,真是奇怪。’”
陳略微吸了口氣,“視頻游戲里如果你在網上隨機遇到一個玩家,將會是段不好的體驗,”他說,“你認為對方會是個混蛋,對吧?”
我點了點頭,仍然沉浸在奧古斯汀以及從一開始坐下和這位工作室的中國游戲開發者談話就感受到的神奇當中。
“但是聽著:我們沒人生下來就是個混蛋,”他說。“我相信經常并不是玩家真的是個混蛋。是游戲的設計者湯他們變成了混蛋。如果你每天都在殺死其它人,怎么可能成為一個友善的人呢?所有的主機游戲都是關于互相殺戮,或者同時殺死對方……你沒看到嗎?是我們的游戲讓我們變成了混蛋。”
在他的最新游戲《風之旅人》正式發布的前幾天,陳和我在離舊金山莫斯克尼中心幾百米遠的一家熱鬧的咖啡館里共進了午餐。去游戲開發者大會(GDC)中途停下來買食物的人們響亮的談話聲填滿了這里。
陳說話用的是計算機極客的方式:安靜而又睿智,有些人會認為這是神經質地傲慢。但他的語言像一個虔誠的傳教者一樣,為了呼吁游戲設計者們創造更好系統從而可能創造出一個更好的線上世界,而向他們傳遞人文主義的精神。
在我們的午餐談話中不止一次我在胳膊上摸到了雞皮疙瘩。陳,就像一個20世紀60年代的音樂記者說的那樣,有靈魂。但是這顆心從何而來?將這位設計者引領至此的又是怎樣的旅途呢?
【歷險的召喚】
14歲的時候,坐在上海的一個小公寓的床邊的陳星漢放下了手柄哭了出來。
“在我可以讀什么或者看什么上面,我的父母嚴格得難以置信,”他告訴我。“我只能接觸到有限的小說、電視和電影,這部游戲是第一個讓我感動到流淚的媒介。那是我第一次哭,如此深入而強烈。我從未有過如此的經歷。”
《仙劍奇俠傳》在中國RPG史上就像《最終幻想7》一樣。它關于愛和失去的劇情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現在再去回想,我發現這個游戲膚淺而又老套,”他說。“但是這是第一次有媒介給了我這樣的沖擊,讓我愛上了它。”
陳通過這些眼淚得到了宣泄(這一話題在我們的對話中他提到了多次),擦干眼淚,他感受到了一種讓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的安寧。“我發現我自己再問:我想過哪一種生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我為什么在這里?在那之后我感到自己成為了更好的人”
“然后我開始審視未來,我決定我要將我的畢生用于幫助他人體驗我剛剛感受到的經歷。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將會通過游戲實現,但是我知道這將通過某種東西實現。”
在他生命的前22年,陳沒有離開過上海。
他的童年充滿了限制:現實的,社交的和雙親的。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讓他沒有兄弟姐妹,這個國家沒有來維持退休計劃的省或者公司,撫養雙親的全部責任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為了(畢業后)獲取良好的收入,在學校取得成功的壓力巨大。對于陳這樣重點班的有天賦和才華的年輕學生來說則更為之甚。“這是個冷酷無情的系統,”他告訴我。“每個學期班上最后三名的孩子將會被淘汰。我在的是這樣的一個精英班級,所以如果被淘汰進入了一個‘普通’班里別人會把你稱為失敗者。”
限制,競爭,排名:陳成長過程中的所有的社會系統也都在大多數視頻游戲中盛行。奇怪的是他的創作中這些都失蹤了。我向他詢問,是否是這些成長過程中這些現實的和心理的限制使他遠離了競爭的、基于任務的游戲。畢竟《花》被設定在了鄉村間,章節之間點綴著呈現城市公寓中枯萎的花的短鏡頭,或許是因為在上海的時候夢寐以求的自由,讓他的最新作品,《風之旅人》,成為了一個完全沒有多人競賽內容的游戲。
直到現在為止,陳一直用著溫和的語氣交談,停下來等待每個回應,偶爾會把問題拋回給我。但看得出這個問題讓他變得煩惱起來。“我是個競爭者,”他說。“我玩并且愛玩競爭的游戲。你知道,我在高中的時候是一個格斗游戲的冠軍。我在大學的時候是《星際爭霸》的冠軍。我也有在玩DOTA。我喜歡贏。我熱愛勝利。至于做游戲,并不是我愛和平的游戲。我做這種游戲,也是因為我喜歡贏。對我來說,一個人的偉大與否要看他們對社會做的貢獻。游戲產業并不需要再多一個射擊游戲,它需要帶來啟發的東西。
我向他詢問,是不是他的競爭性格意味著他希望能在游戲設計上“取勝”,以及是否他去探索一個較少被探索的領域也是為了提高這一幾率。
“是的,”他微笑著回答。“對我來說痛恨教育系統也毫無用處,我在教育系統中存活了下來。”
【試煉之路】
我們在水牛城燒烤餐廳吃飯,這也是事先計劃好的。陳告訴我這是他八年之前第一次去GDC時吃第一頓飯的地方,所以他帶我來這里。被14歲那年《仙劍奇俠傳》帶來的改變一生的體驗影響,他決定要成為一名動畫導演,制作像吉卜力工作室那樣風格的電影。
但時在大學期間,他的一些朋友決定要做一個游戲,找來陳制作模型和動畫。“最后我們做了三個游戲,”他說。“他們都是復刻版,當然,但是都是很好的游戲!其中一個是《暗黑破壞神》的復刻版,另一個是像《風之杖》那樣的全3D版的《塞爾達》。
“很有野心,”我說。
“我知道,但時我們完全把它擱置了。”從大學畢業之后,陳進入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電影,很大程度上忘掉了制作游戲的經理。但是當他的講師們發現他在寫代碼方面的能力(計算機科學方面的特長并非出于偶然,他在大學期間學習了這一課程)他被分配進了電影學院的游戲項目中。
陳并沒有和這一決定對抗,而是接受了它,他性格中競爭的一面意識到游戲為他提供了一個競技場,在其中他有可能會比在好萊塢做出更大的成就。
“電影是很成熟(的行業);對于每個想要的每種感受都有對應的類型,”他說。“不論你是什么年齡,類型,國籍和心情總能找到適合你的。但是游戲……你找得到驚悚片,恐怖片,動作片,以及體育勵志片。但時沒有愛情片,沒有劇情片,沒有紀錄片,也沒有生活中的思想實驗。這些都是人們想要在生活中擁有的基本情感,但時在游戲里都沒有。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長大了就不再玩游戲;他們想要體驗到這些但是游戲并沒有提供。
在陳看來,大多數游戲只提供了年輕人感新區的體驗類型,而在人生后期將學習和掌握的相對較少觸及。
“游戲,本質上是我們學習一些東西的工具,”他解釋道。“當我們還是在操場上玩樂的孩子的時候,我們了解了我們自己的身體,并且發現了和其他孩子相處的基本方式。但時隨著你長大,進入少年時期,你參與到了像是籃球或者足球這樣的游戲中。你學到了團隊作業。但是你很少見到35歲以上的人還在玩游戲。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學會了并且精通了這些技能。你看那些年長的人,他們玩撲克。撲克是一個關于欺騙、計算和操縱的游戲;這些是人生后期需要掌握的游泳的技能。高爾夫球是另一個例子。相對于社會鏈接,高爾夫并不是和運動本身很相關。它鼓勵你和別人一起進行互動。”
“我西歐昂新只有三種方式能夠創造對成年人有價值的游戲。你可以從知性方面,讓作品揭示出你之前沒有注意到的關于世界的新的角度。我所見的最接近這一點的是《傳送門》。第二種方法是從情感上:讓他人感動。你可以非常容易地讓孩子感動,但是讓成年人感動要難得多,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成年人感動,就是創造某種和他們的生活特別相關的東西,或者創造某種東西讓它如此的真實以至于可以帶來力量。為了達到這些高度,你需要得到精神凈化。這樣一個成年人在經歷了自身的強烈感情之后,才會開始尋找他自己人生的意義。因此我認為我可以為我身邊的人做游戲。第三種,也是最后一種方法是創造一個社交環境,在其中可以由他人帶來智力上的或者情感上的刺激。只有這三種方法。”
因此陳開始在影視學院學習游戲設計,然后有一年的春天,USC派他去GDC。“當時我還以為每個美國孩子都是像約翰·卡馬克那樣的編程天才,”他笑著說。
“但我為了了解學生做的游戲去了IGF區,然后我恨不得說‘這些游戲都是垃圾!’嗯,我在大學期間做的游戲比這些要好得多。當時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跟他說:‘咱們來做游戲吧,我們可以做得比這要好。’”
當陳和他的朋友回到USC他們就著手做一個名為《云》的游戲,一個被他戲稱為“同盟模擬”的飛行游戲。所有的孩子都夢想著要飛翔,但時對于陳,因為受到了如此多的限制,這一渴望可能比大多數孩子都要強烈。他們兩個把這個游戲放在了網上供免費下載,很快陳就開始收到關于他的作品的電子郵件。
“我收到在日本的人發來的消息,生成他們在玩的時候哭了。有人甚至稱我是個美麗的人,因為我做了這個游戲。所以我沉下來思考:是做什么正確的呢?這個游戲和其它游戲的區別在哪里?我能想到的唯一區別就是這個游戲讓你感受不同。在那一瞬間我認識到這就是我人生的呼喚。我可以去改變人們對游戲的看法,而不是成為一個電影或者動畫導演。我甚至要說我覺得我有責任去這么做。”
【追尋】
2006年,陳第一次被拒絕參與獨立游戲節(IGF)兩年以后,他的游戲《云》在這一活動中的學生展示競賽中勝出。盡管如此,設計者對他的作品卻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游戲,因為它的操作“不直觀”。我問他如果是這樣的話,到底是什么讓玩家產生了共鳴,進而給這款游戲帶來了如此多的關注。“我認為是單純和孤獨,以及同時感受到的自由和傷感,”他答道。
迄今為止,孤立和超然一直是陳的作品主題。我想知道為什么他著迷于此呢?
“我想是因為我們是創造者,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容易變得孤獨,”他說。“藝術家們渴望被聯系在一起。我們想要感到被理解,想要你感到我們發出的聲音被傾聽。事實上我受到了500封關于《花》的電郵……我覺得我說了,有人聽到了。而且因為作為人類,我們通常是孤獨的,所以得到他人接納的渴望才會如此強烈。當人們體驗到同樣的孤獨感時,他們直接的反應是跟人接觸和建立聯系。我能想象到任何一個在創造什么的人正在尋求與他人的連接。”
他直勾勾地看向我:“比如你作為一個記者,你在尋找能夠聽見你的聲音的人,不是嗎?”我咬了一口漢堡。
這種和他人體驗同樣的孤獨感的意境成為了陳最新的游戲核心內容——PSN下載游戲《風之旅人》,一個精確地詮釋了設計者為全新種類的感情體驗創造空間這一愿望的游戲。
但是這個游戲時長兩三小時的游戲經歷了三年的開發(比原計劃多出一年),與原項目相去甚遠。在原始項目中,陳希望能夠喚起的微妙感情難以表現出來。“《風之旅人》本是一個四人游戲,”他解釋道。“四個人提供了許多額外的社交要素。它更加有趣。但是我癡迷于創造兩個人之間獨一無二的連接,而我發現額外多出來的兩個人將破壞這一連接。創作一個有意義的四人游戲比雙人游戲要難得多。”
“我們想創作《風之旅人》的原因,除了最后到達情感宣泄的時刻,還有希望能在兩個人之間創建真實的鏈接。我這么做是因為大多數人現在都說:社交游戲很火爆。但是沒有其他的游戲是真正在兩個人的情感交流的層面上達到社會化的。在幾乎所有的游戲里,兩個玩家之間僅有的交流是子彈和數字。在Facebook上更多的是數字,在PC和主機上更多的則是子彈。
“所以作為一個設計者,我想看看我是否能夠創造情感交流。起初我們搭建了所有典型的協作機制。拯救他人,治療,一起開一扇門,諸如‘你站在這里,我站在那里,然后什么東西開啟了……’然后我意識到這些仍然是機械的交流。為了真正的交流感受,你需要讓玩家為交流情緒感受做好準備。”
陳向四周看了看,轉向了GDC會議中心的方向。
“我將會解釋,”他說。“當我在會議中心漫步時我在思考我需要在何時到達何處。我處于一種任務解決模式。我對社交并沒有興趣。在大多數視頻游戲中也正是如此。大多數的多玩家體驗是關于解決任務的。但時如果玩家在任務解決模式中,他們并沒有在交換情感連接的正確思維框架里。所以為了讓他們準備好,我們不得不移除掉關于任務的所有內容:從《風之旅人》中移除掉所有的任務和謎題。這樣一來,玩家將更可能會為進行社交做好準備。”
他停頓了下。“然后我們努力讓你感覺到孤獨。在這個精神層面上,玩家開始尋求連接,或者接近與他們相像的某人或某物。這就是我們做的。我們除去所有的東西,為的是創造一個玩家可以在其中交流感情的環境。”
我指出,陳像是要通過去掉這些機制來嘗試著復現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出現的社交互動。但是沒有必要說什么或者盡量對著什么談話,這是一個有趣的嘗試。這有意義嗎?
“圣奧古斯汀曾經說過,”
陳星漢放下了他的漢堡,溫暖而又堅定地注視著我。
“奧古斯汀說:‘人們會為了尋求驚奇冒險攀登至高山之巔,會為了沉浸在驚奇中而佇立凝視海洋的遼闊。但是盡管每個人都是個奇跡,他們在街道上與他人擦肩而過時卻毫無感覺。沒人能看到他人的神奇之處,真是奇怪。’
“在視頻游戲里,有這樣一個假設:如果你隨機在網上遇到了一個玩家,將會是一段不良的體驗。你認為他們會成為混蛋,是吧?但聽好了:我們沒有人生來就是混蛋。我相信一般來說并不是玩家真的是個混蛋。是游戲設計師讓他們變成了混蛋。如果你把每一天都花在互相殺戮上,你又怎么能成為一個和善的人呢?所有對的主機游戲都是關于互相殺戮,或者一起殺死其他人……我們的游戲讓我們變成了混蛋。”
“或者是關于把其他的玩家變成一種資源,用他們來開門之類的?”我插嘴道。
“是的,”他說。“是系統讓玩家變得殘忍,不是玩家自己。所以如果我使用了正確的系統,玩家就是人類,他們的人性就會被發掘出來。我想要給游戲帶來人的價值,并且改變玩家(在網上隨機遇到其他玩家將會是不好的體驗)的假設。”
陳把手伸進口袋中掏出了他的iPhone。“我要給你看一點東西,”他說。
“昨天《風之旅人》在PS Plus(索尼的收費會員服務,付費會員可以享受到提前得到新發布的游戲等特權)訂閱欄里上架了。幾個小時之后,一些玩家在游戲論壇里發起了名為‘旅途的歉意’的帖子。”
“那是什么?”我問。
“自己讀下把,”他說著把手機遞給了我。
這是一連串玩家向他們在游戲中的旅途遇到的匿名玩家的感謝和道歉。
?今晚我真心感激你的幫助。你在我沒有獲取飛行技能的時候如此地耐心。
?我很抱歉當那東西找上我們的時候我因為恐懼藏在了石頭后面。它讓我有點措手不及。
?致我在第五區域里的朋友。我從沒有想過要離開你,只是在跳躍的時候被猛地吹跑了。我想你。抱歉。
?致我所有一起游戲的人:感謝你們從未離我而去。
在我閱讀的時候,陳向我微微一笑。
“我起雞皮疙瘩了,”我說。
【與女神相會】
在我們努力清空我們的盤子的時候,我們的對話稍作停頓。食物已經涼了。
過了一會陳又開始講到:“在《風之旅人》的開發過程中,我有一次痛恨我自己。”
“怎么回事?”我抬起頭問。
“我們做了一個原型,玩家可以互相幫助完成任務。我們的一位開發者建議說加入一股強烈的風讓玩家只能通過互相推動來通過它會很有意思。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任何碰撞判定,所以我們加入了碰撞來實現這一機制。但時你知道發生了什么嗎?當團隊可以在游戲里面互相推來推去的時候,他們做的就只有把對方推進死亡的深淵。及時我們都知道這個游戲是關于積極的事情關于人性的,每個人都只是想要殺死他人。我自己也無法抗拒這么做的沖動。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對我的團隊成員和我自己相當傷心失望。“
“然后我遇到了一個兒童心理學家,我告訴了她游戲中的困局。她跟我說:‘哦,你的玩家們只是又變回了孩子而已。’”
“她是什么意思呢?”我問。
“我問了同樣的事情。她說:‘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他們是沒有道德觀念的。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好壞。所以他們嘗試那些給予了他們最強烈的反饋的行動。’”
“我不明白,”我說。
陳用叉子敲打桌面。鄰桌的一對情侶轉過頭來,不知道是關心還是惱怒。
“一個孩子會這么做,是吧?”他說。“你告訴他們聽,但時他們不僅不停,反而弄得更吵。對于孩子來說,這給了他們最強的反饋和注意。這位心理學家告訴我這就像玩家第一次進入虛擬世界一樣。他們就像孩子一樣。他們不知道規則,所以他們進行那些給予了他們最強烈的反饋的行動。她說:‘讓孩子停止做某件你不想讓他們做的事情的最好方法是你什么反饋都不給他們。’”
“問題在于,每個人都在尋求最大程度的反饋。如果你把某個人推進深淵,反饋是巨大的:另一個人死了,有動畫,聲音,社交壓力和讓她復活的機會。這些事情合在一起讓把另一個玩家推進深淵比只是把他們推進風里更令人滿意。“
“我明白了,”我說。陳停止敲打桌子,那對情侶又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回了漢堡。“那么當你去掉所有的碰撞判定后發生了什么?”
“玩家開始尋找獲取更多反饋的其它方法。互相幫助提供了最多的反饋所以他們改去這么做了。真神奇。”
【英雄的旅程】
我們的會面快要結束了。GDC的樂趣在于沒有圍繞在設計師周圍的公關人士,讓像我們今天這樣自由而不受限制的對話成為可能,但仍會因為出席會議環節而讓我們沒有無限的時間。我們吃光了食物,開始漫步走回會議中心。但我仍然對陳將游戲比作電影的觀點感興趣,對于一個像他那樣的游戲設計者這不是一個常見的比喻方式。他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如此緊密嗎?可能有某些主題視頻游戲不善于表達,或者有某些情感視頻游戲不善于反映。
“不。游戲時一種可以將電影的所有元素與互動化的設計相組合的媒體,”他堅定地說。“對于所有的意義和目的,游戲都會是比電影更適合(的媒體)。但時事實上,游戲現在仍然是電影產業的一個分支。這是個悲劇。我看到了如此多的潛力。我感覺到我在這里有如此多可以做的事情。”
陳性格中競爭性的一面又顯露了出來。
“所以我們嘗試著去做的是去引領情感因素。如果整個游戲行業都專注在興奮和腎上腺素沖擊上……嗯,那我將關注和平,或者愛。這樣我們可以拓展對于游戲可以是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的認知。這就是我為什么做游戲。這就是我為什么踏上了這一旅程。”
歡迎掃描二維碼訂閱【初心咖啡店】微信公眾號,第一時間獲得文章推送。

微信掃這里訂閱【初心咖啡店】微信公眾號